



正德十二年(1517),月舟又主持镌刻 了《伽蓝示迹之碑》,碑文由月舟亲自撰 写,碑阴就是那幅驰名寰宇的紧那罗王线 刻图像(见图2)。紧那罗王,亦称那罗延 神,在佛教里是天上力士之名。慧琳《一 切经音义》卷六称:“那罗延,欲界中天名 也。……欲求多力者承事供养,若精诚祈 祷,多获神力也。”③那罗延出现在少林寺 甚早,寺内至今存有金朝的《妙色那延罗 执金刚神像》,上面刻有那延罗金刚手执 金刚杵的图像及手印和咒语,碑文说,只 要“尽心供养,持此印咒,则增长身力,无 愿不获,灵验颇多”,但并没有作为“武神”和本寺,'伽蓝”而专殿祭奉。④正如 叶德荣所说,少林寺的紧那罗崇拜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在月舟镌立《伽蓝示 迹之碑》以后。⑤
《伽蓝示迹之碑》的镌立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确认了寺内外早就有的一段传闻为事实,即元顺帝至正十一
“张永传”见《明史》卷三。四《宦官一》。正德初,他是权宦刘瑾党羽,后在平定 宁夏安化王朱真镭的叛乱中,与名臣杨一清联手,清除了刘瑾.成为武宗最亲信的掌军 太监。嘉靖初清除谷大用等太监时,永曾降职赋闲,后以功勋卓著,仍然掌御用监、提督 京师团营。张永是明代太监中少数获得正面评价者之一(《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77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温玉成:《少林访古》,29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61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释永信主编:《中国少林寺-碑刻卷》,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叶德荣:《紧那罗王考》,《少林学论文选》,364页,郑州,少林书局,2006。
年(1351)三月紧那罗显圣——“持一火棍,独镇高峰",吓退了进攻少林寺的 红巾军的传说。
其次,从此紧那罗神便顺理成章成为少林寺的护法伽蓝,“永为少林寺 护法气 为此少林寺还营建了紧那罗王殿,供奉三尊紧那罗神像,惜今已不 存。曾见过此殿塑像的清初人景日畛说:“奉神三像,裸体执棍,灵动欲 活……见者无不肃然。”他认为这些塑像“盖秘密类也",就是说这些塑像属 于藏传佛教的雕塑风格。叶德荣也认为是具有喇嘛教特色的塑像。①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此开始,紧那罗神手中的“火棍”(也称“麻 杈”)便成了少林武艺的特色和象征,即假托从那罗延的“火棍”演化而来的 少林棍法成为少林武艺的核心。这一转化非常重要,在中国武术史上有重 要意义。
紧那罗护法神地位的确立以及少林棍法的独尊,幕后有“西天梵僧”的 作用,具体说有匾囤的师父哈麻和包括匾囤在内的一批武僧的作用。作为 一寺之主的月舟对这些内容的确立有推波助澜之功,他亲自撰写《伽蓝示迹 之碑》就是一种表态,一种对寺内“西天梵僧”势力的认同和尊重。
正如前文所言,月舟是禅密兼修的高僧,或者说在藏密之风朝野炽热的 正德时代,他迎合了这种风气,容纳“西天梵僧”在少林的存在与扩张,甚而 收纳了曾投师喇嘛的僧人悟榻(字静庵, 1504-1552)为嗣法弟子。嘉靖十 四年(乙未,1535)至三十一年(1552)之间,悟榻曾两度成为少林寺住持,而 这一时期匾囤正在寺内,也正是他武名鼎盛而学者四方慕名而纷至沓来的 时期,这显然不是巧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②
综上所论,我以为匾囤在少林的活动应起始于月舟主持寺政的正德时
景日畛:《说嵩》,卷二。,《少林紧那罗殿》,45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有研究者认为,紧那罗王殿建于明初,似不确,此殿建于明正德年间的可能性较 大。
温玉成:《小山禅师及其法脉南传》,《少林访古》,30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
社,1999;叶德荣:《宗统与法统 以嵩山少林寺为中心》,42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期;正德以后,嘉靖皇帝崇尚道教,藏密顿转衰落,少林寺“西天梵僧”的势力 也随之悄然式微,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匾囤及其追随者大抵游移于少林与 峨眉之间,这两地都有相当数量的匾囤弟子,长期在寺外活动者也不乏其 人。匾囤在再一次去峨眉的途中圆寂,弟子普明等将其归葬于他人生的起 点少林寺,相信这是他的遗愿。笔者以为,为匾囤在少林剃度并取法名为悟 须的人就是月舟文载。为时不久,可能主要出于对武艺的追求,匾囤选择了 脱禅入密之路,投师于某位喇嘛门下,或即程宗猷所说的“哈麻师程宗猷 在《少林棍法阐宗-纪略》中说:
元至正间,红军作难,苦为教害,适爨下一人出慰曰:惟众安稳,我自御 之。乃奋神棍投身灶炀,从突而出,跨立于嵩山御寨之上,红军自相牌易而 退。寺众异之,一僧谓众曰:若知退红军者耶?乃观音大士化身紧那罗是 也。因为编藤塑像,故演其技不绝。嗣有哈麻师者,似亦紧那罗王之流亚, 曾以经旨授净堂,以拳棍授匾囤。匾囤尝救人苗夷中,苗夷人尊而神之。
“哈麻师……以经旨授净堂,以拳棍授匾囤”,净堂是谁?暂无答案,但 必定也是一位通晓藏密的喇嘛,是哈麻师教旨的主要继承者。按少林字辈, “净”是第二十二世,比十五世“宗”字辈晚七辈之多,故“净”字辈僧人大抵活 动在清康乾之间。所以可以肯定“净堂”是法号,不是按字辈排序的法名。 笔者揣测这位“净堂”,就是前面讲到的月舟的入室弟子静庵悟榻,可能是他 的别号。悟榻是月舟以后具有密教背景的少林寺住持,他是“悟”字辈,与匾 囤是师兄弟关系,二人同为月舟弟子,又同受哈麻师密传,一受经旨,一受拳 棍,可谓一文一武,珠联璧合,堪称哈麻师与月舟文载事业的主要承续者。① 当然,截至目前,这只是笔者的推想,还需要得到史料的证实。程宗猷在《少 林棍法阐宗-总论》之尾又一次说道:
①叶德荣:《宗统与法统——以嵩山少林寺为中心》,42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2010;温玉成:《少林访古》,30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苟能心得手应,巧运力先,冠之以刃,则歼丑虏,壮皇图,于紧那罗王之 圣传,喇嘛僧之秘授,庶不忝矣。
这里又一次强调了匾囤在拳棍上得到的“喇嘛僧之秘授”。哈麻师是一 位“似亦紧那罗王之流亚”的颇有神秘色彩的喇嘛,关于他,我们一无所知。 温玉成曾有所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某位有“大宝法王”身份的藏密高僧,但缺 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只能期待史料上的突破。①无论如何,一位藏传佛 教的喇嘛传拳棍给匾囤,特别是棍法,匾囤又传给少林寺内外的许多人,经 三四代人继承传习,,终于形成明末清初的少林棍法体系,这在从来都具有多 民族文化交流融会特点的中国武术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例证,不能 不让人倍加关注,其中有许多未发之覆还在等待着我们去解读。
再来考察一下匾囤的弟子们。
匾囤的活动空间相当大,从学武艺的僧俗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应该很多。 目前所知,他有一些俗家弟子,如太监张暹、卢鼎、高才等,还有王寅和程宗 猷、程子颐等程氏宗亲,但为数并不算多,他的弟子还应该以僧徒为多。他 有少林寺、峨眉山和京城的吉祥庵三个活动点,这应该是他传习拳棍的主要 场所,但从学的僧徒究竟有多少,以何人最具代表,对此我们所知不多。
就以往所知道的,匾囤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首先是少林寺十二世“洪”字 辈的,如洪转、洪纪、洪记等,为数不多,但可以确信都是出类拔萃的武僧,在 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其次以十三世“普”字辈居多,前文曾多次提到的, 加上叶德荣录自少林碑刻中的,计有普明、普云、普心、普香、普根、普照、普 存、普风、普盈、普觉、普敬等②;还有一位为《少林棍法阐宗》的卷首写赞的普 行,此人事迹不详,但从他与程宗猷、程子颐的关系看,多半也是一位有根基 的武僧;还有一位叫普恩的,应属于匾囤峨眉系列再传弟子中的佼佼者,我 将专节论述。“普”字辈以下,有十四世“广”字辈的,他们算是匾囤的玄孙
温玉成:《少林访古》,309、31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叶德荣:《宗统与法统——以嵩山少林寺为中心》,17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2010。
辈,首先是程宗猷的师傅广按和尚,此外见于少林碑刻的还有广学、广福、广 欢、广海等。“广”字辈武僧甚多,有名的如广美、广顺、广化等,多是曾经奉 调出征的僧官,不但武艺超群,而且还通晓治兵与用兵之道。但这些人与匾 囤有何关系,武艺上有无师承关系,这是目前不清楚的。①
显然,匾囤的弟子不会只有上面所举述的,以少林寺和他本人的影响之 大,不可能只教过这么多人,或者说只有这么多追随者。
前面讲到,少林寺清乾隆四十一 年(1776)«重修少林寺千佛殿记》碑,是 清人磨去明代一通碑的碑面文字后再重 新刻上去的,碑面原刻文字已无从考知, 但碑阴内容却侥幸保存下来,且相当完 整。重要的是碑阴的上端有一幅僧人的 侧身线刻肖像,身披僧衣,毛发苍然,样 貌高古,在整个碑体上居于正中间的位 置,显得很突出。一般认为这又是一幅 达摩像,但笔者以为不是达摩,而是匾 囤,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僧人造 像出现碑刻上,是释道碑刻中常见的,在 少林碑刻中亦非个例,如刻于万历六年 图3匾囤石刻画像(少林寺藏碑拓片)
(1578)的《无穷禅师小像赞碑》就是例
证。②而匾囤画像的发现,在少林武艺史上则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它不 仅使我们对匾囤的真实状貌有了亲切的了解,也使匾囤和尚有可能成为少 林寺历代武僧中唯一一位有灵塔、有碑传,又有画像的高僧,其历史地位一 下子凸显出来,以往的清冷孤寂一扫无余。
被磨去的碑阳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新昌王的《匾囤和尚碑》,
叶德荣:《宗统与法统——以嵩山少林寺为中心》,18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2010。 ,
释永信主编:《中国少林寺-碑刻卷》,18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叶德荣即持此见。但笔者以为有可能是杜栾的碑文中提到的由某位住持撰 写的另一块碑,也可能是另外的碑。笔者的理由是,新昌王碑早在乾隆十三 年(1748)«少林寺志》刊行时就已注明“不见",而碑阳内容刻于乾隆四十一 年(1776),前后相距近三十年,虽然失而复得的可能也会有,然而毕竟不是 常有的事。再者,在新昌王碑的碑阴为匾囤造像,并刻上大量僧俗弟子的名 号,这不大合乎碑刻通制,也缺少了对“金汤檀越”徽藩王应有的礼敬。还 有,此碑体量相当大,依据拓片测量,高220厘米,宽120厘米,原碑正面的 文字量应该相当大,内容应该比较多,既出自本寺住持之手,就可能涉及密 教和武艺,甚而会有太多密教色彩,所以招来磨去重刻的厄运。遗憾的是, 这通一直遭遇冷落的碑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没有被收入《中国少林 寺-碑刻卷》,叶德荣认为这就是新昌王碑,并直接称之为《匾囤和尚碑》;笔 者心存疑虑,建议不妨名之为《匾囤画像碑》,一则借以彰显匾囤在少林史上 的历史地位,二则借此纠正它与碑阳乾隆刻字在先后主次上的颠倒关系。
《匾囤画像碑》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匾囤画像碑》主要由匾囤画像和许多僧人的名号组成。画像的右侧是 以御马监太监朱颌、张暹为首的六名太监的名字;左侧是以锦衣卫实授百户 赵自党为首的四名锦衣卫官员。再往下,除了京都无量庵住持性海、五台山 宝林寺常惠等六位僧人法名外,其他的名号基本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 分是所谓“本山执事”,即少林寺的各级管事僧人,领头的是大和尚退隐悟 纳①,以下是首座、都提举、提举、都提点、提点等一系列执事僧人,其中包括 著名武僧、任修造监寺的周参、副司广美、点座洪纪等。第二部分是“两廊海 众”,即本寺一般僧俗徒众,总数230多位,其中包括了周、洪、普、广、宗、道、 庆七个字辈,还有镇、能、维等非本寺属系的僧人,广案(按)、宗猷亦在其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部分“大峨眉山”100多位僧人的名号,他们的字辈比 较杂乱,有属于少林字辈的周、洪、普、广、宗、道等僧人,也有非少林系的镇、
叶德荣:《宗统与法统 以嵩山少林寺为中心》,42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慧、常、圆、真、惠等,我们暂时说不上这些僧人所属的寺院和宗统,其中还有 很大的研究空间,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少林与峨眉之间的密切关系。这 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明显与匾囤个人的联结作用有关,但匾囤又为什么热 衷于建立这种关山阻远的关系?在宗教和武艺的交流传承上又有何种因缘 与细节?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第四部分是刻在左下侧的以“落发小 师”周会、周清为首的“周”字辈僧俗五个弟子的法名,以法孙洪梅为首的八 个,,洪,,字辈法孙的法名,再往下是标明,,都侍者,,的以普觉为首的八个“普,, 字辈法曾孙,以广玉为首的五个“广''字辈法玄孙,总26人,加上最后署名 “立石”的普明,共27人。显而易见,这27位僧人,含周、洪、普、广四辈人, 是匾囤最亲近的传法弟子,是匾囤武艺的最重要的承继者。
《匾囤画像碑》排列有序的僧俗名号多达数百人,很难说这些人都是匾 囤的武艺弟子或再传弟子等,但其中确有一些少林武艺的代表人物,这显示 了明代少林武艺鼎盛时期的恢宏气象。其中时任“修造监寺”的周参,即大 名鼎鼎的少林武僧竺方周参,曾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司明文调用截 杀,领僧兵五十名,征师尚诏。……尽忠于国,丛林见得忠义”①。详细解析 这个名录,是一项繁难复杂的工程,需要在叶德荣《宗统与法统一一以嵩山 少林寺为中心》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寻绎考证,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 也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故而搁笔于此以待方来吧。
四、匾囤的俗家弟子王寅
匾囤有两位重要的俗家弟子,一位是王寅,另一位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程宗猷。两位都是徽州人,所不同者,王寅曾得匾囤亲授棍法,程宗猷则年 辈稍晚,本人并没能赶上匾囤,棍法似主要是从匾囤的弟子们学来。王寅一 生偏文,大抵是一个高才博学而落拓不羁的文人,对所学少林棍法似乎并没 有太在意,至少没有在传播和整理上做过什么。程氏则生当明末国是日非、 天下将要糜烂的时代。他深怀报国之心,训练宗亲,结为团队,积极谋求为
温玉成:《少林访古》,29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国家出力的机会,结果无功而罢。但他的心志不衰,晚年在族人帮助下,将 平生所学少林棍法编绘为图谱,刊印行世,为后世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古典武 艺资料,在武术史上功莫大焉。本节先来考察一下王寅其人,后面再对程宗 猷及其《少林棍法阐宗》作专题讨论。
王寅,字仲房,一字亮卿,晚号十岳山人。明徽州府歙县人。父亲经商 淮北,王寅生于淮,但后来还是回到故里。他是一个极具才华的人,能诗喜 兵,文武兼长,但科场不顺,始终没有出仕的机会,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县学生 员。因为高才博学,名望甚高,交游也很广,所以曾经投身有同乡关系的名 将胡宗宪幕下,与一时俊杰如戚继光、汪道昆、徐渭、郑若曾等都有交往。特 别是与汪道昆过从甚密,在当时的徽州文人群体中,王寅始终受到汪道昆的 崇敬,被引为知己。王寅有较多的传记资料存世,自己撰有《十岳山人集》, 分《诗集》四卷和《文集》四卷,可惜《文集》已经不存,只有《诗集》四卷被收入 《四库全书存目》。此外晚年曾辑乡人诗为《新都秀运集》两卷,论者以为“持 论颇偏”,也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他的诗在明代诗人中颇享高名,入清 后用心搜集故国诗人之作的钱谦益和朱彝尊分别在《列朝诗集》和《明诗 综》、《静志居诗话》里,对其有很好的评价,特别是钱谦益,称其诗远在汪道 昆之上。
武术界最早注意到王寅的是唐豪先生。唐豪曾写过一篇叫《王寅》的札 记,不妨引录在下面,以见这位武学先贤视域之广。
《万历歙县志-文苑传》:“王寅字仲房,歙县王村人。''康熙《徽州府志》 及乾隆《歙县志》列寅于隐逸。府志传云:“少负气,晓大略,贯通阴符之学。 弃诸生,北学于李梦阳不遇,受拳技于少林僧而还。后与戚继光游,入胡宗 宪幕。幕客多谄事宗宪,寅独佑之,多所匡正,然终以未究其用,郁郁不得 志,乃一泄之于诗。晚岁学禅于六峰,六峰谓海外别有五岳"因自号十岳山 人。所著有诗集若干卷,其事迹与史文略同。"按寅事迹,附见于《明史-徐 渭传》,作“余寅"而不作王寅。道光《歙州志-文苑传》引万历、乾隆《歙县 志》、康熙《徽州府志-王寅传》,断为一人而姓名有伪。不佞尝亲赴王村,考 查《王氏谱牒》:“廿三世寅,字仲房,邑庠生,生于正德丁卯。"卒年不详。
《清一统志》五八卷《徽州府王寅》:“闻少林僧匾囤习兵仗甚精,之少林, 受其术归,而尽破其产。''《清代禁书编目四种-十岳山人集》四卷:“查《十岳 山人集》系明王寅撰,寅在嘉靖中尝游胡宗宪幕府。其诗虽多作于隆、万以 前,但其中如卷一:《塞上前》三首、《饮马长城窟》一首、《庙漠重九边》一首、 《燕京再送伯玉司马》一首。卷二:《恒山歌俺答图》。卷四:《科兴》八首、《辽 阳兵变》一首。均多偏谬,应请抽毁。
上面的引文出自山西科技出版社的《唐豪文丛-太极少林考》,编者附 注云:“一九三七年中国武术学会版,唐豪自藏本。”可惜新编的《唐豪文丛》 错字甚多,我手边无唐氏原本,只能参照唐氏引所用的原书来稍作校理,如 《唐豪文丛》引《清一统志》五八卷“为国”二字,应是“匾囤”之误;“尽破其文 夸”为“尽破其产”之误,等等,不一而足。唐先生此札所引多为方志,其他重 要的传记资料并未涉及,也没有对王寅与匾囤的关系有所关注。而一个重 要的成果则是唐先生亲自到歙县进行过调查,读到《王氏谱牒》,得知王寅生 于武宗正德二年(丁卯,1507),这个年份很重要,使我们有了王寅一生行实 的起点。
汪道昆曾撰《王仲房传》,见载于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八,应该是最具权 威的王氏传记。①汪道昆字伯玉,徽州歙县人。出身巨商之家。是当今方兴 未艾的“徽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汪道昆与张居 正、王世贞同榜进士。后以文章名世,与文坛泰斗王世贞并称“两司马气 又 与戚继光有密交,是戚继光一生事业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同情者。②汪道昆写 的王寅传为许多著作所引用,除了地方志以外,就连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 传》也是节录汪传而稍有损益而已。《王仲房传》比较长,我们只节引其中相
汪道昆:《太函集》,第一册,606页,合肥,黄山书社,2004。此文也被黄宗羲收 入《明文海》卷三九六《传十-文苑三》(黄宗羲:《明文海》,卷三九六,《传十-文苑三》, 第四册,40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附汪道昆》,73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关的一部分。
余家食,业已闻王仲房;比释事归,乃益相习。王仲房者,吾郡中俶傥人 也。父贾淮北,纳高氏姬,举仲房于淮。仲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气勃 勃,自负具文武才。时李献吉居大梁,以著作倾当世士,而少林诸僧习兵杖, 则扁囤最精。于是仲房驰一骑,谒献吉大梁。会献吉留关中不至,居大梁一 月,则之少林。扁囤遂以其术授仲房,什得五六。及还歙,补县学生。…… 其后仲房弃诸生籍,周游吴楚闵越名山,远览冥搜,不遗余力。……及海上 用兵,仲房客督府尚书胡公所。诸客率谄事督府,仲房以谬谓独闻。督府多 疏节,又不纳仲房言,竟以败。仲房西入歙,家犹故贫,就里中营佛子轩,好 佛愈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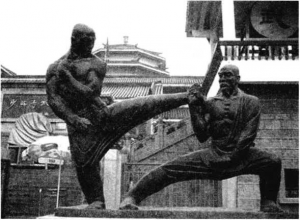
关于王寅在少林寺学习武艺的经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十 岳山人王寅》也有记述,内容与汪传略同:
寅……少年俶傥自负,具文武才,以高才为诸生祭酒,辄弃去不顾,北走 大梁,问诗于李献吉,不遇。闻少林寺扁囤习兵杖最精,则之少林,受其术, 什得五六,归而尽破其产,辞家远游。①
两传中提到的李献吉,即明代中期诗文大家李梦阳(1472-1530),祖籍 甘肃庆阳,明代文坛复古派“前七子”之首。他主张文章学两汉,古诗学魏 晋,近体学盛唐。认为“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以复古为己任气一时影响很 大,士人翕然跟从,但后世评价不一,抨击之声亦多。②王寅原本是专程到开 封投拜李梦阳问诗的,不巧梦阳远去,在逗留中听说少林寺匾囤和尚兵杖最 精,乃单骑奔走少林,求艺于匾囤,“扁囤遂以其术授仲房,什得五六”。康熙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5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丙集,《李副使梦阳》,上册,3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徽州府志》说他“受拳技于少林僧而还”,应是浮泛之词。此事发生在什么 时候?王寅生于正德二年,若以他此年25岁计,当发生在嘉靖十一 年(1532)前后,匾囤正当壮年。在汪道昆的笔下,匾囤的武名竟与李梦阳的 文名相提并论,亦见当时影响之大。王寅“什得五六",说明他在少林寺的时 间并不很长,凭借才华,大略学了一些而已。汪道昆与少林寺也有一定联 系,现在还完整保存在少林寺的《幻休润禅师塔记》,就出自汪道昆之手,时 当万历十四年(1586)。此事亦载《太函集》卷六O,可证明汪道昆说“少林诸 僧习兵杖,则扁囤最精”也是确有了解,并非但凭耳食。①钱谦益生当明末, 虽为东南文坛盟主,可能出于对天下祸乱将起的忧虑,他也非常关注民间侠 义武勇人物,多有交往和接纳,比如他与吴殳武艺上的业师石电(敬岩)就有 交往,石电战死后,他撰写了饱含深意的《石义士哀词并序》②。所以汪、钱二 人关于王寅在少林寺从匾囤学武的记述是出自学者的斟酌之笔,不同于近 世以来民间拳家和钓名射利之徒漫无边际的附会之谈。
王寅的文集已经不存③,我们在《诗集》中找不到与师从匾囤学习棍法相 关的诗作,这令人不解。从诗集看,王寅对武艺和兵器有着浓厚的兴趣,写 过不少与此有关的诗,吟咏对象有剑有刀有弓矢,还有丈八矛,可谓品类繁 盛。其中《丈八矛赠樊大》一首就写得很有意蕴,颇有存史价值。诗云:
锦囊探赠愧黄金,交结虚君寸心剖。羽书夷虏报纷纷,忧解明王正赖君。
汪道昆:《太函集》,第二册,1254页,合肥,黄山书社,2004。
钱谦益:《初学集》,卷七八,下册,16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金星辂《文瑞楼藏书目录》卷九记有王寅《十岳山集》四卷,未知存否(金星辂: 《文瑞楼藏书目录》,卷九,1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烈士定应图不朽,早期一战立功勋。①
这是一首值得仔细玩味的诗。王寅自称儒而不腐,弱冠攻文好武,似乎并没 能坚持下来,读其诗作,毕竟还是文人气十足。虽然曾有过以韬略用世的抱 负和一段少林学武的经历,终究际遇不顺,中年习禅,晚景落寞,读他“七十 自寿”的一组词,除了自嘲以外,再也没有“英气勃勃”的感觉。这首诗的描 写对象是樊大,似乎是一位沉沦江湖的枪家,手运长矛,叱咤纵横,荷矛跨马 如履平地,显然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军旅武艺家,不同于“周旋左右,满片花 草”的表演型的民间把式。值得注意的是两点,即我所说的“存史价值”,一 是他的枪法属于明代六合枪主流的杨家枪,与戚继光采入《纪效新书》卷十 《长兵短用说》的枪法渊源相近。“杨家”的根脉历来说不清楚,但多有托之 于宋代杨令公的,聊备一谈,难以深究。二是他这个姓,“樊”姓,让人有所联 想。明唐顺之《武编》讲明代陆合枪各家,有老杨家、老樊家、孔凤家、济宁吏 家等,其中有“老樊以为滚手迟一着,只两手心向下拿定竿子救”的说法;又 有“樊封闭移后脚左右”等语。②唐顺之所说的“老樊”是否即王寅笔下的“樊 大”?或者樊大乃是“老樊”家族的一员?这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可惜资料 阙如,只能期待找到破解的钥匙。
关于少林寺,王寅写有《五岳歌五首》,其中之一是写嵩山的,但并没有 提到少林寺和匾囤。诗云:
我怀在嵩岳,二室相低昂。
宜卧有石床,铜跳如存温玉浆。
吾祖游栖常此中,道人接上浮丘公。
王寅:《十岳山人诗集》,卷二,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七十 九册,18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
唐顺之:《武编》,前集,卷五,《枪》,影印本,792页、79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有孙今日愿相从,学弄凤笙彻碧空。①
总体而言,王寅赴少林求艺于匾囤,可见匾囤当时武名之盛,但就王寅 本人而言,他似乎并没有专注于少林棍法,“什得五六”是文人的饰词,不必 视为确评。王寅从小就喜好武艺,以后也保持着与一代名将戚继光的交往, 同一些江湖武人也有联系,保持着对兵刃的浓厚兴趣,然如此而已,没有什 么更深刻的内容。②隆庆六年(1572),时任蓟镇总督的戚继光曾邀请王寅至 蓟州游玩,王寅接信后非常高兴,立即辞别杭州诗社诸友北上,并写下《戚都 护约游塞上留别社中诸友》诗:
都护渔阳一札传,址头醉酒兴翩翩。未消弱冠谈兵气,先赋长城饮马篇。白发谁知轻万里,黄云有待出三边。风沙何用愁新暑,苗剑寒霜自荡然。③
他由开封入燕④,抵蓟州(今河北省蓟县)后,曾受戚帅之邀一起登山观 景,纵览塞上秋色。戚继光写下《秋日邀山人歙王十岳、越叶一同、莆方浮 麓、文学郭海岳同登三屯之阴山》的五律诗以纪实。不久,王寅返乡,戚继光 又有《送王山人南还》的七律一首,情意真切,诗风高古,是戚氏《横槊稿》中 的佳作,诗曰:
王寅:《十岳山人诗集》,卷二,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七十 九册,17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
王寅诗集中有《寄倪石洲兼怀亡友王武师》、《匣中剑赠毕汝光》、《买刀篇》、《席 上谢徐太守子与解赠佩剑》等诗作,疑王武师、毕汝光都是民间武艺家。
王寅:《十岳山人诗集》,卷四,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七十 九册,26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
王寅的诗《梁燕二子歌》序云:“隆庆壬申予赴大将军之约,由大梁入燕。”(王寅: 《十岳山人诗集》,卷二,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七十九册,199页,济 南,齐鲁书社,1995)。
天风万里过仙槎,滦水光摇彩笔花。
慷慨已知凌大漠,艰虞何用问悲笳。
乍见白发乾坤短,忍听骊驹道路赊。
秋雁图南江国近,边臣愁绝久无家。
王寅返途经北京,见到在京为官的老友汪道昆,汪道昆也写了《仲房赴 戚将军约顷自塞上还新安取道都门赋此为赠》七律二首,有“少年侠气喜谈 兵,垂老犹堪塞上行。何处射雕夸羽猎,有时饮马出长城”建边关乘兴赴轻 车,兴尽归来意自如”等句。②三人友谊之深,是明史一段佳话。然而这时的 戚继光是手握重兵的总督,汪道昆是兵部侍郎,王寅则依旧是诗酒为友而浪 迹天涯的一介布衣,好友的关爱徒增他内心的凄楚,这是可想而知的。王寅 晚年可能隐居在黄山深处,与渔樵为友,啸吟度日。好友李言恭的赠诗有 “王生白发掩蒿莱,空负人间八斗才”之句。③几年后,得知王寅辞世的消息, 戚继光写下《祭王处士》一文,表达了他对王寅一生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惋惜, 其中有言:
浏览1,01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