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郁永河还在《稗海记游》卷中 说:“君不闻鸡笼、淡水水土之恶乎?人至即病,病辄死。凡隶役 闻鸡笼淡水之遣,皆欷嗽悲叹,如使绝域。水师例春秋更戍,以 得生还为幸。”认为这是个近乎蛮荒的地方。
但早在郁永河之前一百年,此地就早已是个海上贸易的重镇 了。一五九七年,万历二十五年,《明实录》载:“福建漳泉滨海, 人藉贩洋为生。前抚涂泽民议开番船,许其告给’文引’于都东 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这是针对当地行之已久的海上 贸易行为予以合法化、规范化,纳入官府管理。所以出海贩贸需 要获得官方许可文书,以便抽税盘验。而所认可的合法经贸地 区,即包括“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城、高址州等处,共 引一百十七张”。
当时所称西洋,指“暹逻、柬埔诸国,其国产苏木、胡椒、 犀角、象牙诸货,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夷 人铸作银钱独盛。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物相抵。若 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春明梦余录》载傅元初疏)。西洋, 指今南洋一带。东洋本应包括日本,但因正值倭乱,使明人观念 上把日本排除在经贸往来的范围外,只指菲律宾群岛、文莱一带
为东洋。淡水与鸡笼,亦属于此一范围,故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 志》"厅昭引《谈荟》云:“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络、沙瑶、 呐哄单、美洛居、逐、鸡笼、蜘/
鸡笼、淡水在整个东西洋贸易活动中,又有个特殊的位置, 因为它距漳泉最近。乾隆年间《海东剩语》卷六说:“有某把总者 云:曾驻防上淡水。福州近海渔人,于五月初四夜,网取海鲜, 顺风而渡,及晓,即至上淡水。”似海行只需七八更便可抵达。 不但平时漳泉一带渔民来往频繁,更是东西洋贩贸者要将货品运 入中土的门户或前哨点,也是货物的集散转运要地。
但由于朝廷实施海禁,于是这些货品便成了 “私货”。想把 私货运入内地,须靠两种方法:一是文的,以交通官府、纳贿献 金为手段,把货贩入内地;另一种则是武的,靠走私偷渡,强行 运入。《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徐学聚疏云:“海禁不通,则方 物不至。每值东西洋船私寄数金,归索十倍。稍不如意,则诬为 漏税。”讲的就是地方官吏借机勒索敲诈之状。据说其时“拷掠之 毒,怒尽骨髓”。因为该 地民众本来就以此为生、 以渔捞贩贸为业,如此作 为,其虐民可知。何况, 官吏还自营私贩,“又私遣 人丁四出越贩,动经年岁, 搜求珍异,假国用以入私 囊”,人民怎能服气?官 逼民反,遂只好自求多福, 靠自己的本事走私偷渡, 强行货贩了。
这样,就醐了海盗。
海盗,在此时有两种 意涵:一是因海禁,故凡“贩洋为生”者,其实都是定义上的海 盗。二是因政府既不保护贩洋为生者,贩洋者海上的安全,便须 仰赖海上武力集团,或自己结成武力集团。而贩殖所获,须要销 售转运,又为政府所不许,或遭政府所剥削,则势不能不依本身 之武力强行输运,此则为实际的海盗。两者在晚明,受客观政治 环境之影响,渐渐混为一谈。以致鸡笼、淡水等海上贸易奥区, 渐竟成了海盗之窟穴。
《明实录》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年)即载“巡抚福建刘尧诲 以海寇林道乾警报闻”。林道乾的大本营,就在鸡笼、淡水。
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志》封域志建置部说:“嘉靖四十二 年,流寇林道乾掠近海地,都督俞大猷征之,追至澎湖。道乾遁 入台,大猷不敢进,留偏师驻澎。道乾旋遁占城。澎之偏师亦 罢,设巡检以守澎湖。万历间,海寇颜思齐据有台湾,郑芝龙附 之。”占城,在今越南。林道乾大抵往来于台湾越南一带,而其 势自嘉靖间已盛。
从这段记载也可知道当时海寇与日本的关系匪浅。俞大猷抗 倭事迹中,有一大部分就是与这些海寇相周旋。抗倭也者,所谓 的“倭”,就包括林道乾、颜思齐,乃至后来的郑芝龙。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载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巡抚江右 命都御史刘一焜奏谓:“浙地滨海,所在防倭。温、台、宁三区, 俱属要冲。鸡笼、淡水二岛,正对南鹿,尤当日夕戒严者。”温 州、台州、宁波区域,倭患最为严重。南鹿在温州区,其所以日 夕戒严尤为谨慎者,正因鸡笼淡水为“倭”之根据地也。
次年,八月,同书又载福建监察使李凌云奏说:“问其何故 侵扰鸡笼淡水?何故谋据此港?何故擅掠内地?”因当时我国已 获琉球通报,说日本想占领台湾北港。这北港,其实就是淡水。 乾隆十年《重修台湾府志》风俗志,番社风俗条引《名山藏》 说:“鸡笼淡水夷,在泉州澎湖屿东北,名北港,又名东番。永 乐中,郑和入谕诸酋。”明朝自郑和以后,大抵已将台湾视为领 土的一部分,虽未建置,但已如“荒服” “藩属”之类,任其自 治。故对日本人想实质占领或侵扰台湾仍甚介意,所以才有这 样的诘问。
“侵扰”跟“占领”并不一样。依海盗的习惯,生涯本在海 上,陆地不过作为暂时止泊、休憩、补给、维修、积藏货粮之 处。他们进攻内陆,大抵也只为了掠取财货,并不想占领久居。 “倭寇”在浙江福建一带寇掠,即属此种。鸡笼淡水,同样也曾 遭掠劫。但这个地方也提供给他们休憩、止泊、积货、贸易的便 利,因此也成为他们的根据地。
可是这是海盗式的傍水扎寨,而非真正进行占领统治。明朝 说/上年琉球之报,谓汝(指日本)欲窥占东番北港,传岂尽 妄?”则就是说日本有意夺占台湾,如丰臣秀吉欲夺朝鲜一般。 次年,巡抚福建右副都御史黄承玄奏云:日本“家康物故,其子 代之,欲有事于东番”,即指此而言。这就不是海盗所能干的事 了。大概日本政府有运用当时海寇的海上势力,实施国家领土扩 张之谋,故明朝防倭才显得如此慎重。而防倭一事,纠缠在海岸 人民生计、远洋贩贸、国防战略之间,也才会愈弄愈复杂,难以 董理拿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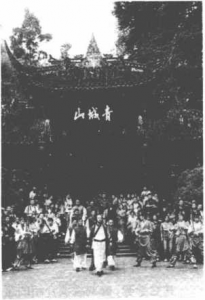
鸡笼淡水的地位或角色,在其中也就格外暧昧了。一方面, 它是海寇聚啸之地,明朝不但无法有效统治,而且还视之为敌 区。所以“鸡笼淡水二岛正对南鹿,尤当日夕戒严”;林道乾遁 入台湾后,俞大猷也不敢轻率进兵。《闽海赠言》载林有标《沈 宁海将军自淡水奏捷,两汛无警,小诗赋赠》云“受降城筑未经 秋,捣穴宣威至淡流……”也明显以攻入淡水为直捣敌域。从这 一方面看,淡水不啻域外,乃匪区也。可是,另一方面,《明实 录》载万历三十五年福建巡抚刘学聚语,称“诸夷益轻中国,以 故吕宋戕杀我二万余人,日本声言袭鸡笼淡水,门庭骚动”,又明明以鸡笼淡水为中国之地。
林道乾、颜思齐、郑芝龙等海盗,即游走于这个暧昧的空间 中。既是中国人,又是倭寇;既是商贩团队,又是劫掠者。
郑成功以后,海盗的角色大变,原本被明朝视为“倭寇”之 一的郑家商盗船队,一转而成为明朝的国家武力。原本傍水扎寨 式的占据,变成了领土统治。屯田拓垦,经营台湾,也成功地使 其海洋事业转型为农耕形态。这时,倭人才暂时停止了对台湾的 染指。海上贩贸固然仍在进行,但台湾是以国家的身份在担任东 西洋货物转运站这个角色的。
明郑灭亡后,台湾作为清朝国家体制中之一部分,情况并 无改变。但清朝的办法,是更强化其农耕性,削弱其海洋商贸性 格。即使商贸,亦只以台湾与内陆之关系为主,减弱台湾在东西 洋贸易中的地位。
因此,迟至咸丰元年,洋船始能在淡水鸡笼依商贸易,官 照商船征税。其余香山、中港、鹿港、鹿耳门、打狗及各大小口 汉,一律禁止洋船贸易。道光三年,打狗港及鹿耳门才开禁。见 《淡水厅志》赋役志,关榷部。
可是,台湾在海洋经贸上拥有的地位及力量,并不能因此而 完全遏止,故而在清朝统治期间,海盗依然是不断出现的。康熙 六十年,《东征集》载《檄淡水谢守成》云:“昨情擒获孽丑黄来, 供称台湾山后,尚有匪类三千人。皆长发执械,屯聚山窝,耕田 食力,又有艘舰往来。”可见此即海盗之不服清朝王法者。
这类海盗,大约不少。嘉庆以后,蔡牵之声势则最惊人。
清朝与蔡牵麋战多年,相关战报、奏折,均见于《台案汇录 辛集》。起自嘉庆元年,止于十八年。
蔡牵的船队来往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在台亦无固定根据地。 十年闰六月兵部奏称:“该匪为内地舟师跟追剿甚严,屡次窜来 台洋躲避,兼可截掠商船,视为利薮。” “台湾地势袤长,滨临大 海,自淡水沪尾起至南路之东港止,计程三千余里。港汉纷歧, 在在可以通舟。匪船乘风伺劫,或南或北,往来靡定。”即指此。
其势似甚大。嘉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许文谟上奏称二月间 进犯盐水港的海盗就有“贼匪数千人”。七月,兵部资料载鹿耳 门大捷,“夺获并击沉匪船二十一只” “击毙、淹毙股头贼目匪犯 一千六七百名” “搜获伪印一颗,上刻'王印正大光明’六字”。 此役清军共调动船四十二艘,又有义民洪秀文捐助船四十五只, 才能合击成功。蔡牵船队此次仅出动三十三只,所以寡不敌众。 但由其数量,亦可以想见他的声势并不下于清朝台湾水师。滋扰 甚久而一直难以平抚,不为无故。
蔡牵船队固然袭泊之地不定,但淡水一直是他经营着力之 处。故嘉庆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军机大臣谕:“朕闻淡水沪尾以北 山内有膏腴之地,为该逆素所窥伺,此时或又窜往,亦未可知。 赛阿冲可派兵前往,相机办理。”同年三月廿六日,闽浙总督玉 德奏也称:“上年十一月内,(陈花)随同蔡逆盗船驶到淡水滋 事,该犯在沪尾上岸打仗。”同年八月三十日,刑部为内阁抄出 福州将军赛阿冲奏会亦云:“淡水沪尾地居极北,逸匪尚未尽获。” 十三年,正月廿四日,赛阿冲又奏:“朱渍帮船,三十余只,先窜 至鸡笼洋面。……又匪船窜至沪尾。”十八年十二月廿一日,闽 浙总督汪志伊题本亦载:“陈刚,原任闽浙督标右营外委,管带兵 丁拨付台湾剿捕蔡逆,留防台湾沪尾海口。”
这些记录,都显示了蔡牵的根据地之一就在淡水。清朝水师 之防务,也以淡水最为吃重。因此,嘉庆二十一年八月,福建巡 抚王绍兰奏,说巡阅台湾澎湖兵营,分别等第时,台湾水师中、 右、左三营及沪尾水师操练最精,为第一等。台湾城守营,“露 舟甲、喝玛兰二营,布阵连环,紧凑得法,藤牌跳舞,亦属便捷”, 为二等。水师南路则弓马软弱,为第三等。这种排序,正反映了 当时防务吃重的程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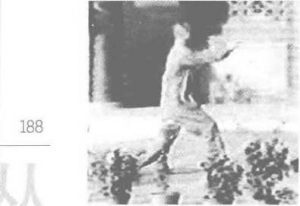
依清律,凡逮到海盗:“江洋行劫大盗,立斩枭示。又洋盗 案内,接赃仅只一次者,发黑龙江给打牲索伦达呼尔为奴。又, 被胁服役、鸡奸者,杖一百、徒三年。”(嘉庆十一年三月廿六 日,闽浙总督玉德奏折)处罚不可谓不重。可是海盗之势依然 如此之大,只能说是官府断了人财路,所以趋利者不绝,络绎 于海上了。
据嘉庆十年四月十四日闽浙总督玉德奏称,当时总兵吴奇贵 “身为大员,于海洋匪徒肆扰,自应认真奋勉缉捕。乃竟心存畏 恿,屡催不应。丧心病狂,实出情理之外”,应予革职。此即可 见当时海盗声势足以令官兵畏战。
后来经王得禄等人戮力整顿、奋勇力战之后,情况才好转, 蔡牵等人之声势逐渐销戢。但海上之盗,并不止息。嘉庆二十五 年(一八二。年)十一月初九,有上谕云:“所称淡水之沪尾、鸡 笼及喝玛兰一带洋面,又有匪船游奕等语。从前洋面大帮贼船往 来肆劫,剿捕多年,始行净尽。比年洋面肃清,何以忽有匪船游 奕?王得禄系水师提督,洋面皆伊所辖,责无旁贷。此等匪船若 不及早扑灭,听其勾结,又成大帮,必致滋蔓难图。着该提督即 分饬舟师出洋擒捕。”这就可以证明海上之盗是不曾止息的。
而且,嘉庆皇帝还没有弄清楚的是,这时再度死灰复燃的小 股海盗,乃是新海盗时代的先声。带来的,乃是比从前“洋面大 帮贼船”更巨大的力量。那就是以西方国家力量来叩清朝海关关 口的新海盗时代!
嘉庆帝在发了上面那道上谕之后不久便过世了。道光继位,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姚莹《中复堂集•上孔兵备书》有云: “胛板夷船,以贩鸦片禁烟,为粤省驱逐,窜入闽洋。总督、巡 抚、水师、提督,严檄沿海文武官勿任停泊。自本年三月至鹿耳 门外,郡中禁严,遂使至鸡笼。而淡水奸民恃在僻远,潜以樟脑 与易鸦片;水师任其停泊,经时不更驱逐。此中弊情,固显然 矣。”这就是指英国来贩鸦片的事。
以后经历鸦片战争,列强更番入侵,法国海军甚至进攻淡 水。这些事,读近代史者无不知之,我就不备述了。
摘要
台湾的宜兰地区虽开发较晚,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始 有吴沙等入垦,武风却素称兴盛。宜兰武风兴盛的因素,主要为 开垦御番之需,其次是作为安定地方之力,再次为分类械斗之用。
清朝嘻玛兰时期及日据时期,官方对武馆均采严格管制立场, 直至光复之后,武馆管理才纳入正轨,武馆的发展才受到法规保障。 武馆管理的法规,主要是一九四九年台湾当局公布的《台湾省各县 市国术馆管理规则》,订定国术馆成立与经营的规范。
宜兰县的主要武术团体为一九五二年成立的“宜兰县国术会” 及一九六七年成立的“宜兰县体育会国术委员会”。“宜兰县国术 会”近年来少有活动,“宜兰县体育会国术委员会”则为宜兰县国 术活动主要推动单位。
宜兰县传统武术门派以宜兰河为界,有溪南、溪北之说。 大致而言,溪南武馆重视门派,严守家法传统,以德义堂、勤 习堂为代表;溪北武馆讲究革新求变,主张吸收众家之长,以 太祖忠义堂、礁溪狮团为代表:1 .德义堂:德义堂分布全省, 以五祖拳为主,号称宜兰最大门派,曾在宜兰各处传授三千名 以上弟子。2.勤习堂:宜兰勤习堂传自云林四湖吴金河,属白 鹤拳系。3.太祖忠义堂:林金狮所传,属太祖拳系。4.礁溪 狮团(金鹰拳):振兴社系,目前以茅埔、港仔尾、林美、洲 仔尾四团为主。
宜兰县武馆之传统经营形态,主要为庄头武馆及国术馆两 类。庄头武馆以庄头为中心,弟子为附近子弟,武师则多半聘自 外地,流动性较大。国术馆则以武师为中心,固定一地设馆,弟 子慕名而来。时至今日,武术传承逐渐转移至小区及学校的武术 社或武术队。其招生方式、对象、经费来源、师生关系以及武馆 的社会角色,均大幅改变。
展望宜兰县武馆之发展,有几项新的方向。分别是:(一) 小区化、学校化之传习;(二)正式比赛之激励及套路标准化; (三)养生、气功、整复等武术新路向;(四)本土化、民俗活动 之热潮。这几项方向,是宜兰县武馆发展的新挑战,也是契机。
一、宜兰县武术源流
宜兰地区虽开发较晚,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始有吴沙 等入垦,武风却堪称兴盛。同治元年至光绪十九年间,宜兰武举 人即有李辉东、周振东、胡捷登(礁溪乡武暖庄人,同治九年庚 午科中式第二十六名)
锦华、潘振芳、陈文德等计十三人,武秀才亦有林陈祖(礁溪街 人,四围堡下四围区长)、谢长生(礁溪街人,光绪乙亥科武秀 才)、林兼材(礁溪街人)等。传习武艺之风,遍及各乡里。宜 兰武风兴盛的外在因素,主要为开垦御番之需,其次是安定地方 之力,再次为分类械斗之用。
阵头表演为武馆训练成果的正式展现场合,融合舞狮、拳 术、兵器、阵式与鼓乐而成,或称为“舞狮”“狮阵”。
宜兰狮团以礁溪最负盛名。据《礁溪乡志》载,礁溪狮团 源自白云村份尾阿琴师。阿琴师俗称“大箍吟”师,少居林美山 麓,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迁居白云村份尾聚落,务农维生。 阿琴师见当时治安不佳,盗贼四起,民心惊惶,乃思筹设村庄自 卫组织,于是创立武馆,收徒三十余人,分别教以拳术,包括叉 手、粗拳、直箭、三叉、大马、下粗拳、上中下洗马、童子拜观 音等二十余套拳,及长短兵器。三年后,学习人数已多,遂组成 舞狮团,表演民俗阵头,形式略似宋江阵。阵头表演中的拳套演 练顺序大致如下:
其中八卦阵除武术演练之外,更象征 镇煞驱邪,对于以庙会为主要表演场合的 阵头而言,特具意义,亦更显重要。
阿琴师的弟子在礁溪二龙村、三民番 割田、壮围乡五间等处,各自组织狮团, 传承武艺。
宜兰地区的分类械斗,依性质可分为 六大类:一、省籍械斗,如闽粤械斗;二、 府别械斗,如漳泉械斗;三、姓氏械斗, 如陈林李三姓械斗;四、职业械斗,如挑 夫械斗;五、乐派械斗,如西皮福禄械斗。
其中西皮福禄的乐派械斗为宜兰特有之械斗类别,并与武 馆发展息息相关。日据时期宜兰厅曾调查并作成《西皮福禄之历 史调查及目前之情势暨视为两派首领者之视察要领及与他厅(基 隆、顶双溪)同党者之关系(气脉通之与否)》之报告。调查报 告说明西皮与福禄两派产生之背景与习武械斗之状况曰:
音乐是由中国古代所传,距今四五十年前,在宜兰厅下 尤其在南部地方盛行音乐,有数庄连合或一庄分为数派以 举行音乐比赛。竞赛到了极点,终于发争斗杀戮事件。此即
为西皮福禄为名产生党派之起因也。
其后(大概于道光年间)西皮福禄互相培养子弟,而
另一方面又设置集义社、暨义社等,大练武术,两派互相蓄 势对立应变。大有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之状况。……当时之清 朝官吏亦大为,或以威力压抑,或以道理试行和解,但未至 根绝之态势,而经常小斗不断。至光绪十九年,福禄派仰仗 陈辉煌(阿里史庄武学官),而西皮派则仰仗黄绩绪(宜兰 街十六炭街黄举人)。互相挑战,旁若无人,因而横行益甚。
宜兰厅的另一篇报告《西皮福禄之结党纷扰》,更说明两派 为械斗而聘请武师传授武术之事曰:
迨至光绪七年,马桂芳卸任,由彭达孙继任宜兰知县, 因让西、福两党自由弄奏音乐而禁止演戏。一时几乎绝迹 之西、福两党乃重新再唱出歌曲,争斗亦随之而起。自光绪 八、九年双方各结党徒,聘请教师学习拳头槌法之各种武 术及十八般器械使用法,以应时之需,从此两党之仇视欺 压更甚。于光绪十年、十二年在头围、宜兰、罗东等地区相 继斗争,官方虽逮捕一二名处以死刑及其他重罪,但随制随 起,遂至无论如何处理亦无可奈何。
不仅于民间有此种党类事件,在官衙及地方绅士亦有 参加其党派者,福禄推举营官陈辉煌为其首领,西皮乃拥 戴举人黄绩绪为首领。
可见乐派之械斗为武馆发展之重要助力。
日据时代早期乐派械斗仍然严重,当时各村庄均有三馆之 设,一是子弟馆(即音乐团),二是狮馆(即武术馆),三是学 馆(即私塾)。狮馆由武师成立,聚集青壮年教授拳术,及长棍 短棒、大刀铁尺、藤牌双刀等兵器,进而舞师跳桌等。日本官方 为防止对立与械斗情势蔓延,强化治安,严格管理,终使西皮、 福禄之械斗绝迹。日本官方亦禁止民间狮馆之组织,于是武术活 动只能暗中进行。
少数例外如台北县知事倡立武德会,以“裁成在台之武人”, 这当然是应和日本官方的门面话。原文作“栽成”,当为“裁成” 之误,邱心源曾有一文记录其事,颇能表现狮阵表演之貌与武馆 于日据时期之处境,曰:
及迎神赛会,凡武人各集 数十人,名曰狮阵。扎竹 枝外蒙五色帛为狮子形,以 二人妆狮子为跳掷状,余 则拥以矛盾刀杖,列次各展 拳勇技击之术。 自改隶 以来,武人技击亦自弃,然 拙者巧之机,屈者伸之始, 且文德与武功不容偏置, 武人尤须作其壮气,使之修德,而入于有勇知方之范围。于 是,村上台北县知事为会长,倡立武德会。以栽(裁)成在 台之武人。未几,知事以官制改易,解组归朝。于是武德会 员,相率呈其技勇,送别于淡水馆,并摄影为记。(《台湾惯 习记事》中译本)
文中所谓“自改隶以来,武人技击亦自弃”之说,当然是为 日人之严厉管制文饰之词,但可见日据时期武馆生存的困难。
此外,文章开头所云:“凡武人各集数十人,名曰狮阵。扎 竹枝外蒙五色帛为狮子形,以二人妆狮子为跳掷状,余则拥以 矛盾刀杖,列次各展拳勇技击之术。”说明狮阵为武人所集、狮 头作法、舞狮的基本方式及拳术兵器的表演等,则是近百年来大 同小异。
二、宜兰县武术团体
清朝喝玛兰时期及日据时期,官方对武馆均采严格管制立 场,直至光复之后,武馆管理才纳入正轨,武馆的发展才受到法
规保障。
国术馆管理法规与台湾省国术会
一九四九年,台湾省政府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国术馆管 理规则》,开始管理台湾各地武馆。其中规定了设立国术馆的许 可制度,“凡开设国术馆者,应由负责人于开设前填具申请书、 保证书及本人最近二寸半身照片三张暨许可证成本费、印花税 费,向该管警察局申请登记,经查明核准发给许可证后,方得 开办”。此份许可证每年一月应缴回该管警察局查验,并加盖验 戳,然后发还存执。而且于此规则施行前已开设之国术馆,也 应于此规则公布施行后十五天内补请登记领证。此规则还限制 设立和参加者的条件,凡具有下列各项情事之一者,不得开设 国术馆,也不能充当国术教练或参加学习国术:一、无一定住 所或居所者。二、素行不良者。三、患精神病者。不仅如此, 自开办日起,负责人每三个月应“将参加学习来宾之姓名、性 别、年龄、职业、住址呈报该警察局备查”。此外,国术馆所用 的武器,不但均须烙印该国术馆名称及号码,备簿登记,并由 负责者直接保管。更严格的是“除练习武艺外,不得借予他人, 非有正当事由不得携出馆外使用”。当然,国术练习使用的武 器,“系指锻炼刀、剑、枪、矛及各种武器而言,枪械不包括在 内”。而且这些武器,“当地警察机关因治安上之需要,得予以 检查或暂时保管及使用”。
这个规则并规定国术馆负责人和国术教师“非领有从事医术 之开业执照者,不得为人医治疾病”。如此一来,武馆的重要经 济来源受到限制。这个限制却受到台湾省国术会的挑战。
台湾省国术会于一九五一年由国术耆老及党政人士二十一 人发起筹备,推举时任台湾省警务处长的王成章将军为筹备会 主任委员,国术名家黄生发、新竹县警察长陈鼐为副主任委 员。当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台北市中山堂第一届会员大会正式成 立,由王成章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台湾省国术会成立后,颁行 伤科及内科之“证明书”。“证明书”成为台湾省国术会创会初 期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当时台湾省国术会入会费为新台币五元, 会费一年为新台币十二元,而医疗证明书一份则需新台币五十 元。因此一九五一年九月成立后,十一、十二月两个月的收入共 一万一千八百一十八元,其中开立“伤科证明书”收入六千四百 元,开立“内科证明书”收入二千二百元,两项合计八千六百 元,占总收入72.77%,重要性可想而知。所谓“伤科证明书”, 是以台湾国术会名义,开立证明书给会员,证明该会员“精医跌 打伤科,接骨入甑,应用各项丹膏丸散,合乎科学卫生,悬壶问 世,济世救人”,因此“合应发给证明,用介病家”。这样的证 明书,提供国术馆执业行医的非官方证书,当然深受欢迎,却 也遭到批评,于是改成“介绍书”。“介绍书”内容为:“查会员 x x x经历祖传师授,熟谙国术拳技,兼精中法接骨疗伤之学, 尤具仁人济世之心。多年以来,嘉惠伤员不可胜计,军民咸沾其 德,而于发扬中华固有文化意义尤深。爰给本书,用为之介。” 进一步担保其拳技、接骨疗伤之学与仁人济世之心,及“嘉惠伤 员不可胜计”,并同样推介给病患。虽然不论证明书或介绍书, 都不能改变《台湾省各县市国术馆管理规则》中“非领有从事医 术之开业执照者,不得为人医治疾病”之规定。然而这样的情形 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才改变。
行政院卫生署于一九七五年发布《国术损伤接骨技术员管 理办法》,确定国术馆接骨疗伤的法令依据。此办法将国术馆从 事跌打接骨者订名为“损伤接骨技术员”,并限定可从事内容为 “国术损伤接骨整复”,而且“不得施行注射或交付内服药品”, 似乎从严管理。然而此办法的结果,是使原有从事接骨整复人 员,能够就地合法,取得从业资格。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凡“于 民国五十六年六月二日前,取得台湾省国术会会员证,经查证属 实者,均得依本办法之规定,向行政院卫生署申请有登记,并请 领国术损务接骨技术员登记证”。持此登记证,即可向所在地政 府申请从业执照。
这显然是为传统国术馆从事接骨工作者大开方便之后门。因 为国术会为依人民团体组织法成立的民间社团,加入会员的条件 十分宽松,只要是对国术有兴趣的初学或外行人,都可以经简单 手续加入国术会,成为会员。且加入国术会时并未考核其接骨整 复能力,换言之,国术会章程并未将接骨能力列为会员加入的必 要审核条件,亦可以会员资格作为申请接骨技术员的唯一条件。 尽管不合理,却给予国术馆生存发展的一股力量。
国术馆最主要经济来源,本即是接骨疗伤,此后更确定国术 馆由“传授武艺、接骨疗伤、弄狮演武”三合一的武馆,转变为 “接骨疗伤为主”的国术馆,传授武艺与弄狮演武的功能,已不 再是国术馆的必要项目。
(二)宜兰县国术会
宜兰县国术会的全名为“台湾省宜兰县国术会”,依章程所 载,其宗旨为“提倡国术效忠国家发扬正义服务社会并团结力量 努力反共”(原文无标点)。
宜兰县国术会是宜兰县第一个国术民间组织,然而近年来迹 近停摆。说“迹近停摆”,有几项因素。
首先,本届是第十届,相对于第八届、九届举办的活动,本 届自一九九七年会员大会结束后,未曾举办活动,因此可谓停摆。
其次,相对于同属国术团体的宜兰县体育会国术委员会、宜兰 县武术协会及台湾省体育会国术委员会之活跃,国术会可谓停摆。
再者,经查宜兰县政府社会科,并无本届国术会资料,仅有 第十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手册,而此手册所列资料均属第九届,至 于第十届资料付诸阙如,自是必然。社会科所能提供数据,仅知 第十届理事长为余添泉,并登录两个联络电话。可是这两线电话 不论白天、晚上、平时、假日都无人接听。社会科人员帮忙试 打,结果亦然。再询问曾任理事长的黄培基、曾任监事的简忠信 及会员也是体育会国术委员会理事长的陈正行诸位先生,均无所 悉,只知国术会停摆多时。
后来联络上理事长余添泉才知道因为工作在台北,长居台 北,宜兰虽有亲人,毕竟山隔路远,事务繁忙,与宜兰国术界少 有联系,也是必然。联系尚且罕有,遑论推展国术会会务、举办 活动了。
访查之初,对此历史悠久的会竟似凭空消失,深感意外。而 主管机关宜兰县社会局除九七年手册外,竟无其他任何数据,堪 称怪事。后来才知道,宜兰县政府找不到宜兰县国术会资料并不 是新闻,早在一九七七年就曾因为资料遗失在报上喧腾一时。当 时曾有报纸标题为:
浏览85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