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菊怒放的时节,离开上海飞往澳大利亚,悉尼城却正是温馨花 香的仲春,我是应澳大利亚太极学院的邀请,前往讲学访问的。两个 月里,在院长许荣楚、许荣安先生的陪同下,先后到堪培拉、墨尔本、 悉尼、珀斯、阿德莱德、布里斯班等六个城市讲课、辅导、联合表演、参 观访问,亲身领略了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武术的感情。
许荣楚先生是一位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中年华裔,他向我介绍了 这所学院的简况:现有300多名教练、2 000余名学员,分布于全澳各 洲,尤其是各大城市。建院九年来,先后有五六万人在学院学过太极 拳。从澳大利亚中国旅游公司的吴先生那里得知:澳大利亚太极学 院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武术学术团体之一。九年以前,由弟弟许荣安 在悉尼创办,当时只是一个仅有几十人的太极班。
我第一次讲课是在堪培拉。尽管备课时间较匆促,我却并不紧 张,只是担心一连讲四小时,这些异国听众有无兴致坚持到底?讲课 时,由许先生亲自担任翻译,当我连讲带示范地讲完了中国武术的性 质、特点和内容时,台下140多名听众竟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当 然,许先生的翻译也是很有妙道的。接下来我又陆续介绍了气功、太 极拳要领和推手,并带着大家亲身体会一下,众皆趣味盎然。尤其是 推手,竟使大家一下子爱不释手,三个半小时在不知不觉中一晃而 过。最后大家要求我介绍半小时的中国书法,并当场演示。我的蹩 脚书法就只好来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我试图结合太极、 气功来表现书法的要义和修身养性的原理,他们感到很能接受。课 一结束,木仅那几幅不成体的字被争抢一空,总教练诺德还对我说: “回去后我们也要练'永'字八法!"
回到悉尼,便有人从堪培拉打电话来,要求来悉尼补上未听的课; 远在二百英里以外的纽卡索分院还特意开了专车载着学员来悉尼听 课。这样,悉尼的讲课地点便不得不临时改换,以满足更多的听众。
在珀斯讲完课时,一位年逾A旬的老妇人热情地送给我一张印有树 熊的明信片,又拿起一本武术小册子让我签名,说道:“我年纪大了,不能 亲身到中国去,但是我很喜爱东方文化,你们的太极拳太有意思了!"
在布里斯班的一个星期天,我竟讲了六个小时的课。天霭已暮, 有些人还迟迟不大愿意离去,拉住我的手说:“我们过了一个充实而
有趣的星期天,增加了许多难得的知识。"
除讲课以外,通常还要和该院的教练们联合表演。我被责无旁 贷地定为“主角”,自然须尽力而为了。澳方教练们表演的项目有杨 式集体太极拳、太极对练、太极剑、莲花功、导引功等。他们十分注重 配乐,大都是中国古曲,听来十分和谐,节奏与动作很吻合,练得也颇 有韵味。许氏兄弟还亲自表演了在中国学习的长拳、刀术、棍术、九节 鞭和单刀对枪等节目。此外,还有扇子拳、笛子拳,表演者手持其物, 动作倒大都是武术招式,据说这两种拳在解放前的上海时有所见。
访问期间,我曾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有教师、医生、护 士、心理学家、科学工作者等。精神病专家台维说:“还是在大学读书 时,太极拳就对我繁忙的功课起了调节作用,使我精力充沛地修完大 学课程,现在我又把太极拳教给了学生,并研究从精神上如何达到平 衡和放松。”凯尔先生说:“我行医多年,感到太极拳比世界上各种运 动都优越,因为剧烈的运动时常会伤害身体。人们的生活紧张、工作 压力大,太极拳可以有效地消除这种疲劳和精神压力。"
在墨尔本,我曾看了教练们的一堂练功课。从一般的松身到动 气功,到一段段的太极拳,从全体到分小组练,足足练了三个小时,每 人都是汗涔涔的。其中有一位神甫,也是练得津津有味。他告诉我: 三年前,他在街上买了本介绍太极拳的小册子,自己看书习练,可怎 么也学不好,后来进了太极学院才入了门。他认为太极中的阴阳哲 学与教义有相近的地方。他如今还常常在教堂布道时穿插讲一些太 极拳的道理。
在阿德莱德,一位华裔黄医生对我说:“我是一个太极拳爱好者。 这里的一些家庭主妇生活优裕,无所事事,又好吃甜食,造成身体肥 胖,忧心忡忡,没办法,我只好给他们开'太极'这个药方了。”
有位名叫乔娜的老妇人,身患腰痛病,四处求医,尝试了各种疗 法。儿女们各自成家,丈夫又去世,使她在孤独和烦恼中对生活感到 绝望。她偶然在电视中看到太极拳后,便成了一位热衷者。她说: “我喜欢太极拳,并不在于它能否医好我的腰痛病,重要的是它给了 我生活的勇气和阳光,使我敢于面对人生。"如今通过锻炼,她的腰痛 已经减轻了许多。
还有一位名叫玛莉亚的13岁女孩,曾在悉尼与我们同台表演, 一套太极阴阳剑练得颇有风采。许先生告诉我,她原来是个越南孤 儿,六年前一对老夫妇把她从美国的孤儿院里领来,他们认定让她先 学好两样东西:英语和太极拳。如今这两方面她都挺出色,还在一个 以她的身世为题材的故事片中担任女主角。表演那天,两位老人也 来观看,他们表示:有朝一日定要带她去中国一游,把中国的武术看 个够,学个痛快。
这所学院何以会吸引这么多澳大利亚人?许荣安先生的话是最 好的说明:“用适应西方人心理的方法来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
学院把分部撒向全国各城,各城又有星罗棋布的教学点,人们可 以就近学到。他们又把太极拳分成六个技术段,每期一段,六期可以 毕业,不至于望难生畏。他们以健身为宗旨,每周学员来一、两次,会 聚一堂,练拳探艺。舒缓的音乐,优雅的运动,用以消解工作的紧张 和竞争的烦扰。
眼下,人们非但爱好太极拳,长拳类的武术也在兴起。许荣楚先 生说:“这些年来,随着中国武术的传播,华人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古语云“春兰秋菊不同时”,对地处南北两半球的中、澳两国来 说,却是“春兰秋菊亦同时”。你看,太极拳这朵武坛奇葩不也在不同 国度里竞相绽开了吗?
授武在澳大利亚
(一)
1985年10月至12月,我应澳大利亚太极学院邀请,前往该院 教授中国武术。在悉尼机场迎接我的是院长许荣楚及许荣安先 生。他俩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裔兄弟。他们不仅汉语说得很流 畅,而且谙熟华夏风情。该院总部设花悉尼。他俩X陪同我先后 访问了堪培拉、悉尼、墨尔本、珀斯、阿德莱德、布里祝班和高斯芬, 所到之处都有他们的分部。院长许荣楚还告诉我,目前他们拥有 300多名教练和2 000余名学员。学完6期为满,每期发给一个证 书,期满为毕业。8年来,有近6万人参加太极拳的学习,其中有 老师、职员、会计、工程师、医生、护士、学者以及家庭主妇和老人。 我在墨尔本还遇见一位教堂里的神父,如今他已成了太极迷,荣升 为教练。
首都堪培拉不同于悉尼那般繁华,却显得更幽雅、洁净。欢迎宴 会在一家“北京饭店”举行,共有200多人,都是该院的教练和学员。 席间许多人离座起舞。有一对从事工作多年的夫妇,交谊舞、探戈、 吉特巴都跳得很出色,他们却对我说:“我们俩最喜欢的不是跳舞,而 是打太极拳。”第二天的表演中,果然看见他们练的太极拳也颇有味 道。珀斯的总教练贝尼,曾多次获得荷兰空手道冠军,原是移居澳洲 做空手道教练的,如今却深深地爱上了中国的太极拳,成了一名专职 的太极拳教师。
每到一处,都看见太极拳竟吸引了那么多的洋人,开始也有些诧 异。近两个月的访问,才使我明自了个中缘由。
中国太极拳作为一种文化,不仅娴雅清逸,而且有奥妙的拳艺和 拳理。这固然是其中之因,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它也十分适应西方人 的社会心理。那里工作是颇讲求效率的,在工余或周末,就很需要一 种放松的、对身体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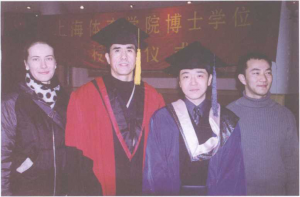 益的活动来消除紧张的疲劳。一位名叫凯尔的 医生对我说:“我行医多年,感到太极拳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它更注 重保护身体,使体内调节取得平衡。”其实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调节 和放松。在那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思想是很疲劳的。来到太极学 院练太极拳,大家来自不同的职业和岗位,交流太极拳艺,有说有笑, -津津乐道,自然对身体有益。对于老年人和家庭主妇却是一种精神 寄托。一位管理老人院的诺贝先生告诉我。在澳大利亚许多老人在 儿女生活独立后,感到孤独和寂寞,而太极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色 彩和阳光。在阿德莱德,遇到一位63岁的朱兰,她说:“我的背痛医 了五年,什么疗法都尝试了,医学上已认为无能为力。在失望中,丈 夫又去世,更平添了忧郁和烦恼。当我从电视上见到太极拳,便与它 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使我的背痛大大减轻,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生 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的确,太核拳在不少澳大利亚人眼中,不仅对 健身有效,而且情趣是很高尚的。
益的活动来消除紧张的疲劳。一位名叫凯尔的 医生对我说:“我行医多年,感到太极拳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它更注 重保护身体,使体内调节取得平衡。”其实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调节 和放松。在那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思想是很疲劳的。来到太极学 院练太极拳,大家来自不同的职业和岗位,交流太极拳艺,有说有笑, -津津乐道,自然对身体有益。对于老年人和家庭主妇却是一种精神 寄托。一位管理老人院的诺贝先生告诉我。在澳大利亚许多老人在 儿女生活独立后,感到孤独和寂寞,而太极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色 彩和阳光。在阿德莱德,遇到一位63岁的朱兰,她说:“我的背痛医 了五年,什么疗法都尝试了,医学上已认为无能为力。在失望中,丈 夫又去世,更平添了忧郁和烦恼。当我从电视上见到太极拳,便与它 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使我的背痛大大减轻,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生 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的确,太核拳在不少澳大利亚人眼中,不仅对 健身有效,而且情趣是很高尚的。
共同的表演是在国家体育馆的一隅举行的。我被责无旁贷地聘 为“主角",而那时刚到异国的我,由于旅途疲劳和住宿不惯,真有些 担心挑不起“主角”的重任。表演前,中国驻澳大使聂成功偕同夫人、 秘书和翻译来了,并特意到休息厅来看望我,嘘寒问暖。我的五个节 目都顺利地练了下来,与其说由于澳大利亚观众的热情掌声,莫如说 亲人在场给了我们精神力量。
澳方教练们表演了集体太极拳、太极阴阳剑、太极对打等。许氏 兄弟还表演了长拳、刀术、棍术和九节鞭。尽管技术水平与我国高手 比还不算高超,但在那里已足让人刮目相看了。尤其是每套节目都 配有中国古曲,动作与音乐又十分合拍,增加了表演效果。其中还有 一套扇子时开时合,每一招式用的都是武术动作。据说旧上海曾有 人练过,不想如今在澳大利亚倒兴了起来O
我在每一城市讲课,来听课的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二三百人,每 次要讲上四个小时,大家听得总是饶有兴味,倒不是我讲得高深,而 是中国文化确实让人着迷,如今还有不少澳大利亚人喜爱上中国菜、 中国书法。最后一天是讲课,院长许荣楚亲任翻译。从武术的特点、 内容讲到太极要领、中国书法。不觉过了四小时,140多名听众没有 一个离去,他们说:“中国武术真了不起,这种课再上四小时也不觉 长。"事过之后,有些未听到课的人打长途电话来问在悉尼讲课的时 间,以便赶往悉尼补听。想不到,武术在澳大利亚也已有了如此的吸 引力。由澳大利亚又可以想到全世界的情景,太极拳运动终将成为 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二)
许荣楚先生介绍说,太极学院总共有300多名教练、2 000余名 学员,9年中先后在这里学习太极拳的达五六万人次。我心想,会有 那么多人参加吗?兴许是“号称"的虚数吧。百闻不如一见。第二天 安排我与在悉尼的教练们会面,并做些技术辅导。走进练习馆,在热 烈的掌声中一看,习武者竟有六七十人之多。他们都身着统一的蓝 色中国式练功服,除了绣有太极学院的会标之外,胸前大都佩戴不同 颜色的徽章。许先生告诉我:佩金属牌者是总教练,佩紫色有机玻璃 牌者为高级教练,佩红色牌者为一般教练,还有不佩戴的为见习 教练。
.他们很注重礼貌,行中国传统的抱拳拱手礼。许荣安先生对我 说,多年以前,中国在澳大利亚被人瞧不起。而今不同了,人们认识 了中国的了不起的文化,武术是其中之一,人们就不能不向中国教练 “顶礼膜拜”。
荣安先生于9年前在澳大利亚开办太极班。当时他只是义务性 地开了个太极班,每天驾摩托车去教学,但是他下决心不向政府伸手 要每周60澳元的救济金。年复一年,太极班扩大为太极训练中心, 至今成为遍布各州的太极学院。
辅导过后,教练们整整齐齐地排队站好,等候由我发给上海体院 的纪念章和明信片,只是我手中太少了。许先生见我面有难色,笑笑 说:“没关系,我们这里等级很严格,只发给总教练和工作出色的高级 教练,这是一种荣誉,大家都有反而不珍贵了。”
总教练乌斯拉,一位德国女性,有着修长的身材。她最早练瑜伽 术,现在太极、瑜伽两者兼习,她对我说:“这次听了讲课,感到太极比 瑜伽术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更深刻些。”一位名叫马克的16岁少年,是 该院的见习教练。他的父母都是太极爱好者。5年前马克患有较重 的哮喘病,体质很弱,父母便带他来练太极。如今他“人高马大”,除 了练太极,还学会了舞狮,作狮身子,躬身在下,非但不觉气闷,还在 台上跳上跳下呢!
悉尼表演中,13岁的玛丽亚表演的太极阴阳剑也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她练得沉着自如,表演能力颇强。许先生告诉我:“前不 久她应邀在一个故事片中担任女主角,一开场便是表演这套剑术。 她在我们学院练了六七年,现在虽是电影明星,却依然酷爱武术。”表 演之后,小玛丽亚拉住我的手说:“看了您的表演,使我对太极以外的 武术也发生了兴趣,希望能有一天去中国学习武术。”
(三)
在墨尔本还未来得及到下榻的旅馆,便先前往电视台拍下一个 新闻片断,并应邀在1. 5X2. 5平方米的小地毯上练两段拳械套路, 这“用武之地”真令人作难了。记得上一场在悉尼的表演是在一个舞 台上,他们问我要不要试试场地,我当时回答说:“没有问题,武术中 有句话叫,拳打卧牛之地,。”而今,果真一块卧牛之地摆在了我面前。 没办法,我只好将原来的动作稍作调整,进三步退两步地练,竟也一 气呵成。许荣安先生高兴地说:“今天我看到'拳打卧牛之地了,! ”
星期天的下午,去看教练们练功。台上总教练布诺带领,台下有 五六十名穿蓝色练功服的教练,足足练了三个小时,个个都那么津津 有味。的确,会练些中国的太极拳,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是很值得自豪 的事。布诺总教练,只有28岁,却十分精明能干,原先是一家出租汽 车公司的司机,而今身价高了许多,成了专职太极拳教练o'
休息时,我与一位名叫托尼的教练交谈。托尼18岁时从高处摔 下来腰部致伤,中年后日趋严重,几乎难于走动,每天要去做牵引。 四年前,他开始学练太极拳,腰疼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现在已不再 去做牵引,只需每隔六周去检查一下。如今他是开载重车的司机,还 可以搬东西。业余时间一心迷在太极拳上,拳术上他已是练拳者中 的佼佼者了。
教练中有一位神父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告诉我,他最早是在街 上购买了一本太极拳的小册子,试着自学,却总不得要领,后来进了 太极学院才逐渐入了迷。他说教义中有与太极拳理近似之处,如今 在教堂里也常引用太极拳的道理讲给人们听。许先生在一旁插话 说:“在我们学院里,他是一名谦恭好学生,在教堂里他是神父,我们 也很敬重他。”
晚上,教练们邀请我到住在郊外的让先生家中吃自由餐。三、五 人一起,边吃边谈,还看大家一起共同表演的录像,气氛融洽又热烈。 让先生是一位棉制品公司的总经理,家中陈设多是东方文化的雅品, 诸如中国字画、龙泉古剑、古瓷器等。他说,太极拳使他有充沛的精 力来工作。现在两个女儿也参加练太极拳了,她们都不爱读书,一直 闲散在家,她们准备把吸烟的恶习戒掉,一心练好太极拳。
澳大利亚来的院长
正当桃红柳绿时,澳大利亚太极学院院长许荣楚先生带领了一 个41人的武术旅游团,来到中国。这些来自南太平洋的远方客人大 都是第一次来华,他们从进太极学院学习太极拳开始,逐步对东方文 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愿望。最早,人们连“太极”也弄不清, 还以为是一道什么中国菜呢。三个星期中,他们饱览了万里长城、桂 林山水、西湖春晓、少林寺塔、曲阜孔庙等风光,观赏了上海体院、沧 州武协组织的武术表演,访问了《中国体育》杂志社……满载着对东 方文化的万千感受回国了。
唯独留下团长许荣楚先生一人,他要留在中国继续深造。
许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从读中文开始,对祖国的历史知晓不 少,虽也是第一次来中国,他的心思却不能在游山玩水上。他要借此 大好机会,拜会中国武术协会、中国武术研究院、商讨中国武术在澳 大利亚的开展及如何走向世界等问题,他还要在上海体院、北京体院 学拳求艺。听说徐州有一个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那里聚集了众 多武术名家和民间拳师,他们毅然决定在那里中途下车,一览中国武 林精萃。不巧,稍为好些的房间均已住满,市体委赵主任向他表示歉 意。许先生却说:“我来这里为了求师寻友,,不是为享受的。”是的,他 的第二个孩子刚出世一个月,他就离家来中国了。既有这么大决心, 何惧吃一点苦呢?
每天凌晨,东方刚刚透出曙色,沙国政老师已在操场上等候这位 远来的“学生"。他要在三天时间里教会许先生形意散手炮和子午鸳 鸯钺,尽管已作了“简化”,这对一个五年前还是一名会计师的40岁 开外的人来说,也是很艰难的。
想不到许先生精力那么充沛,一天要练四次,连看完大会表演后 的饭前一小时也不放过。练了一身汗,房间里却没有洗澡间,他破天 荒第一次走进了大众浴室,而且第一次自己动手洗衣服了。面对困 难,他毫无难色,令人不禁想起秋瑾的诗句:“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 换酒已堪豪
当他顺利地学完了这两个套路时,笑着说:“中国武术真是太丰 富深奥了,我是不可能一 口吃成胖子的。只是我作为院长,必须对武 术有更多的了解。今后,我们学院在澳大利亚推广武术,自然还要仰 仗祖国的支持呵!”
在澳大利亚开拓
在济南举办的国际武术教练员训练班上,又见到了澳大利亚太 极学院的开创者许荣安先生。这已是他第五次来中国了。他的身体 练得更魁梧结实,黝黑的脸膛上,两眼闪着兴奋的目光,对我说:“这 次来中国收获最大,不仅学的东西多,而且学习了教学法和理论。”担 任这次训练班教练的吴彬和于立光两位老师介绍说:“许先生很用 功,每天一大早起来复习练功,这次学的拳术、剑术和棍术都取得优 秀,还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呢!”
许先生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自小喜欢活动:爬树、 游泳,还学会了一点咏春拳,只是当时父亲希望他好好读书,不准他 花很多的精力去学拳。中学毕业后,父亲送他到澳大利亚接受高等 教育。在学校里当了篮球队长。学完之后,他开始在一家公司任职 员,时常感到周围人对华人的歧视和冷遇。他观察了西方社会人们 的心理状态,决心专门学习中国太极拳,1976年后 ,他几次去台湾, 先后学习了杨式太极拳、太极阴阳剑、扇子拳、笛子功等,在悉尼开创 了第一个太极班。他骑一辆摩托车去免费教学,几年后,太极班发展 为几百人的太极训练中心,又成为几千人的太极学院。后来,他把侨 居英国当会计师的兄长许荣楚请来,,将院长的职务让贤给哥哥。
,他几次去台湾, 先后学习了杨式太极拳、太极阴阳剑、扇子拳、笛子功等,在悉尼开创 了第一个太极班。他骑一辆摩托车去免费教学,几年后,太极班发展 为几百人的太极训练中心,又成为几千人的太极学院。后来,他把侨 居英国当会计师的兄长许荣楚请来,,将院长的职务让贤给哥哥。
1980年后,他开婚来大陆学习武术,先后在广州体院、上海体院 学习了长拳、棍术、盘龙刀、单刀进枪等,他深感大陆的武术由政府直 接来抓,技术更规范化,教学更科学化。近年来,他又开始教长拳类 武术,吸引了不少澳大利亚的青少年。
临别前许先生对我说:“别看我在澳大利亚被人称为太极的开拓 者,在中国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小学生。"他拍拍肚子说,“一到中国来, 我的肚皮就练下去了,很高兴。”
据悉,他与兄长回国后,将积极联合其他武术团体,筹备参加11 月间在天津举办的国际武术邀请赛,那时,我们将可能观赏到许荣安 先生的扇子拳表演。
函馆印象
时光如流,转瞬已是隆冬,我却依然难以忘怀去年8月的函馆之 行。的确,日本函馆市的夜景不愧为世界三大夜景之一,令人心旷神 怡;函馆人对中日友好和中国武术的淳情厚意,更令人感慨不已。我 们一行三人是应日本函馆太极拳研究会、老年人联合会和文化之友
会的邀请作短暂访问的。特意赶到东京来迎接我们的是函馆太极拳 研究会会长涉谷道夫先生。他堂堂的额头、一副络腮胡须,脸膛透 红,身躯高大,很富有幽默感,谈话间总可以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O
涉谷先生是函馆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体育教授,对社会体育也 颇有研究和实践。1984年他来到上海和北京,便对中国武术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认定它将是他今后要进行的一项最主要的体育工作。 他学习了武术基本功、少林连环拳、刀术和24式太极拳。第二年又 带着几十人来上海学习太极拳,以后便年年进行武术方面的交往。 而今这个研究会已拥有1 500多名会员,在这个北海道的宁静城市, 竟也兴起了中国武术热。
涉谷教授显然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半年之前就着手筹备这次交 流活动。时间虽短却安排得紧凑而愉快。同时,他又是一位身体力 行的教练,虽然已五十多岁,却一点不迟钝,不仅动作协调,功力和柔 韧性也不差,当我来不及辅导时,他就自愿当起长拳教练,带领一班 青年人练习长拳基本功和套路,俨然一位行家里手。
他告诉我,他曾向我国家体委建议设立中国体育博物馆,武术中 就有很多内容可以向国内外人民展示!他说,目前函馆的人们还没 有把太极拳、长拳等作为竞技比赛项目。在日本,人们更关注于增进 健康和交往。他的观点,不禁使我联想到1985年曾访问过的澳大利 亚太极学院,两者的看法十分相近。自然,世界人民对武术的情感决 不局限于竞技比赛上。如何处理好提高与普及是中国武术推向世界 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函馆,迷上太极拳的大都是些老人、家庭主妇、 职员、医师、老板,也有些中青年人,谈起太极拳都那么津津乐道,练 起来又都那么虔诚。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关堂夫妇了。关堂 文男教授是函馆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系主任,从不多语,却深沉热 情。他对太极拳的兴趣,不仅由于学校体育馆作为太极拳研究会的 活动中心,使他耳濡目染,更重要的是他的夫人关堂绢子迷上了中国 武术,是研究会的骨干力量。她曾先后学习了 24式、48式、杨式等 太极拳,以及32式太极剑、太极连环剑、练功18法等。他们夫妇两 人曾两次来华学习,这次我去辅导.,他们也是早晚每场必到,夫人参 加练习,哪怕已练熟的套路也仍然一丝不苟;先生则帮助安排组织课 堂,课间还寻机摄影,可谓“妇唱夫随”的太极拳迷。
我们曾应邀去他们家作客,雅致而琳琅满目的龙泉剑、中国书画 和中国工艺品,令人赏心悦目。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情,表达了对中 国大民和中国武术的挚爱。在参加辅导学习的学员中,有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每次练习总是站在前排,动作虽不那么松柔,却显出执 著的追求。每每课后,他总有不少问题要我解答。交谈中,得知这位 田中先生的简化太极拳已学一年半,32式太极剑学了两个半月,记 下了几万字的学习笔记。他说目前是“表面上的完结”,需要钻研。 最近他还寄来了学太极剑的笔记,其中将每一动作绘成连续动作图, 他说虽是漫画式的,但对看图学习者却极为方便。我想,这倒是一个 启迪,中国的武术书文字记述大都比较繁杂,作为技术文献可能是必 要的。对看图学习的广大初学者却并不实用,反而容易走入“迷宫”。 今后如果我们能注重连续图解式的记述,以图为主,文字则画龙点 睛,恐怕会备受欢迎。另外还有两位老人也给了我至深的印象,一位 是“文化之友”的会长山内良治先生,他对中国太极拳的兴致是从研 究中日文化中产生的,对中日刀剑交流,他能滔滔不绝地讲一大套。 而老年人联合会会长后藤性信先生则是一位宗教学的专家,他是从 研究中国宗教中,燃起了对富有中国文化象征的武术的热情。
短期的访问。除了友谊、交流,留给我更多的是思索。中国武术 在世界的每一片热土上得以传播之后,该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十、书评与书序
给王俊法《武术双语教学》的序
当中国的都市时尚着跆拳道、空手道、街舞的时候,一批洋学生 却迷恋于中国功夫的“过招这便是当今的国际文化态势,不同的 民族文化既在交融,也在竞争。文化若水,柔却有力,沁透人心。文 化是民族的灵魂,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经济实力、文化实力都不可或 缺。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却不是文化输出的大国。看一看好 莱坞的大片、“韩流"般的电视剧,似乎也感到了我们的差距。
由此,如何利用好我们的文化资源,如何令世界上人们喜爱、向 往和追寻,既为人类造福,也为民族文化的弘扬,便是我们每一个民 族文化工作者所探讨的一个课题。武术是优秀的民族文化之一,它 是在用身体运动讲述中国文化,用他的精美招法和奇妙功力诠释中 国文化。
艾斐先生在《文化的责任》一文中说:“要把优秀的文化推向全球, 其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都应是崭新的,具有说服力、感召力和渗透 力的。"人们是否想到了武术运动也是推介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武术这一身体运动形式,一旦有语言作桥梁,便如虎添翼,不啻为具有 感召力、渗透力的崭新传输形式。中国人不会外语,外国人不懂中文, 将会使武术的传输,尤其使对文化内蕴的领悟和交融大打折扣。
由此,我们太需要懂武术的外国人,也更需要懂外语的武术人。
王俊法便是我们期待的后者。记得23年前在上海体育学院就 读本科的他,说他是一名出色的武术运动员是无愧的。他把武术功 力和技艺熔为一炉,颇为美妙,时常令人激情荡起,为当今不少年轻 运动员所不及。然而当时他的外语水平却极为平平,他告诉我,用了 七年的时间攻读,又到亚、非、欧七个菌家“摸爬滚打”,终于实现了他 的人生目标,在境外教学既能教,也能说,还能练,很受欢迎。
今天欣读他的《武术双语教学》书稿,由衷地为他高兴,这位来自 孔子故乡——曲阜师范大学的武术教师的书稿,将由青岛的中国海 洋大学出版社出版。青岛蓝蓝海水正是2008奥运的水上竞赛圣地, 以此可以呈现给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们,得以成为国际武术文化交 流中的一个窗口。
青岛也是哺育我的故乡,师生之谊,故乡情怀,不禁欣然命笔。
给王岗、王铁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
浏览74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