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袁仲一等编:《秦始皇陵兵马俑》,《秦俑博物馆论文选》,西北大学 出版社1989年版。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
汪宝荣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
《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徐扬杰:《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 年版。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
刘文典撰、管锡华点校:《三余札记》,黄山书社1990年版。
刘文典撰、冯逸等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清]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中华书局1992年版。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清]皮锡瑞撰、盛冬铃等点校:《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 年版。
[清]孙诒让:《墨子冏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
[清]汪继培辑校:《尸子》,《续修四库全书》第1121册影印清嘉庆 十七年(1812)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等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7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清]张玉书撰:《佩文韵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1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28] [清]乔莱:《易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册,台湾商务 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27] [清]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
[26] [明]董说原著、缪文远订补:《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25] [明]茅元仪辑:《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
[24] [明]俞大猷撰、廖渊泉等点校:《正气堂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3] [明]张志淳撰、李东平等校注:《南园漫录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年版。
[22] [元]方回:《续古今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3册,台 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21] [元]陈元靓:《事林广记》,《和刻本类书集成第1辑》,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Q年版。
[20] [宋]卫漫:《礼记集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册,台 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19] [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18]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版。
[17] [唐]李筌:《太白阴经》,《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版据《守山阁丛书》本影印。
[16]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 [唐]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1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13] [北齐]刘昼著、傅亚庶校释:《刘子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
[12]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 ][梁]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版。
[9] [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
[8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 年版。
馆股份有限公司2。()8年版,第39页。
① [清]乔莱:《易俟》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册,台湾商务印书
[7]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清]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 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 [汉]荀悦撰、张烈点校:《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
[5] [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6年版。
[2]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1]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总之,武学是一门渊源深长而又长时间遭遇冷落和曲解的学问,中华武 学的重新建构必须从追根溯源做起,然后循其脉络,贯通条理,才能正确把 握它的发展规律,在对传统精蕴的不断深化了解中,找到恰当的创新点。正 如古人在谈到对《易》理的正确认识时所说的:“六十四卦各有微旨奥义, 错综条贯其中,非循其脉络,得其会通,乌能窥易之蕴耶!”①对司马迁《史 记》中剑道文化的探索与解读,本质上就是一个寻求古典武学演进历程的工 作,是类同于“窥之蕴也”的工作。当然这是颇有难度的事情,以我浅陋的 学力,所做必多疏失,如果能有一点引玉之效,亦足以称平生之愿矣。
君子以玉比德,是取其“温润而泽,仁也”等一系列美好的象征意义, 孔子条分缕析,讲得非常清晰。而司马迁以剑比德的着眼点是什么呢?他没 有讲出来,留给后世一个颇费思量的话题。多数人的联想,以剑比德无非取 其光明正直、高冷峻峭的外观特征和器用品质,加上制作之精和应变之巧, 都绝非轻而易举就能掌握的高难技能,精通其道者从来都少之又少,这又增 加了它珍稀而高贵的贵族般气质。佩剑与佩玉确实有所不同,佩剑者未必一 定要精通剑法,但终究是要有一点敢于“亮剑”的心理素质和勇气的,所以 剑不是什么人都能佩带和敢于佩带的,《史记》记载的佩剑者几乎没有一个 是凡庸之辈。围绕剑的这些特质,古人写过很多铭文和诗歌,而我以为最为 司马迁倾情的应该还是《大戴礼记》里托名周武王的那个《剑铭》,即所 谓:“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说到底剑是兵刃,主要功能在于 “防检非常”和“击刺之效”,所以“行德”是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背 德”则是倒行逆施,害人害己。剑经常扮演着权力的象征,对握有生杀之权 的天子和权势人物而言,更加需要强调“动必行德”,滥用兵刃杀害无辜是 伤天害理的恶事,所以古人一再强调“夫兵者凶器也”,反对轻举妄动,更 反对穷兵跋武,这正是司马迁“君子比德”的寄义所在,由此而推延到兵 法,推延到整个“谈兵论剑”。
在司马迁心目中,剑是一种兵器,却又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载体,围绕着 剑,产生了一群特立独行的人,演化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气象。特别是在剑 的全盛时代,它的文化意蕴和张力,大大超出了兵器的单一属性,升华成为 一个高峻宏大的精神容器。所以,在各式各样的兵器中,司马迁唯独给剑赋 予了 “与道同符”和“君子比德”的崇高评价,这是非常耐人玩味的文化意 趣。正由于此,才奠定了剑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武术史上的显赫地位,在它 的军事功用早已衰落了的千载之后,仍然保持着典雅、高贵、神秘的表征意 义,受到人们的敬重。这一切显然与司马迁的总结与评介是有关联的,只是 过去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我看来,后来被士大夫群体所津津乐道的“书 剑并重” “剑胆琴心”之类,其实都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起点孽衍出 来的。
毫无疑问,剑和“剑道”曾经是我国古代武学的核心内容,对整个武学 体系的结构生成和延续发展都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个核心的形成,有着跨地 域多学派凝聚融合的基本趋向,也有着流派上的差别,特别是南北的分野和 交融。它的学理中吸纳有道家、儒家、墨家和兵家等各种思想因素,后来也 包括了司马迁《史记》的载述与阐释的因素。我深信,《史记》对先秦剑道 精神,特别是秦汉剑道精神的深刻表述,对西汉以后剑道的持续延续产生了 深刻影响。魏晋以降,剑道文献散佚殆尽,以“比剑”为核心的技术传承日 益虚化。在这种大势之下,《史记》几乎成为唯一保存了许多先秦和秦汉剑 文化与剑道精神的经典典籍,成为后世搜寻古代剑客踪迹和击剑掌故唯一的 渊薮。
[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信出版社2016年 版,第219页。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 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5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502页。
《史记》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巨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为立言主旨的太史公,目光敏锐,胸襟宏阔,在政治、经济之外, 还收载了大量的文化现象和许多细琐的社会事务,即太史公所谓“网罗天下 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②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战国到秦 汉时期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③这其中就包括了我国汉代以前的剑文化。 剑文化汉以后虽然依然不绝如缕地存在着,但全盛是在汉代以前,是在春秋 到两汉的数百年间,汉以后则日渐式微,直至走向缥缈虚玄之途。庆幸的是 《史记》为我们提供了剑的全盛时代的许多细节,如果没有《史记》的载 述,我们对我国历史上的剑与剑道文化的了解将是残缺而肤浅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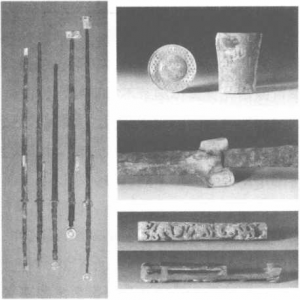
六、结语
作为一种古老的自杀方式,“伏剑而死”或“伏剑自刎”在汉代还延续 着。汉以后随着剑作为兵器的功用逐步衰微,“伏剑而死”也很少见了, 大致宋以后基本上绝迹于史籍。我们对“伏剑而死”的细节尚无了解,我推 想,这是否与短剑的长期存在有关系?它很有可能与短剑的存在相始终,毕 竟长度达一米以上的长剑不大容易“伏”。《史记》写聂政将死时,“因自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本质上很像是“剖腹自杀”,也可能是当时“伏 剑”的一种形式。此事固然异常惨烈甚至是非常野蛮的,但毕竟确确实实存 在并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是值得我们寻思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王仲荤:《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
顾颉刚:《吴国兵器》,《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李学勤:《青铜剑的渊源》,《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止庵:《樗下读庄》,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徐元诰集解、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孙继民、郝良真:《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黄怀信等编:《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马明达:《说剑丛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
韩巍:《黄土与青铜:先秦的物质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美]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林寿晋:《论周代铜剑的渊源》,《文物》1963年第11期。
论武学与武术文献学
——《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代序
马明达
一、引论
《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上下辑)即将刊印行世。这是一项筹备已 久的古代武艺图书汇编工作,是一项关乎“武学”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在各 方友人的慷慨支持和热心关注之下,历时数年,迭经汰选,总算初具规模, 可以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作为这项工作的主持者,欣慰之余,也想谈谈个人 的一些想法,主要是想围绕“武学”与武术文献学的建设问题谈几点浅见, 望各方博雅有所教正。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武术,近代以来曾经有过相当繁盛的 局面,大致从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出现过几次高潮,只是由于社会背景不 同,高潮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然而武术当下的状况却不能不令人忧心, 特别自两次大张旗鼓的“申奥”活动失利之后,社会对武术的关注度持续下 降。在跆拳道、泰拳、空手道等外来项目的冲击下,武术的生存空间不断萎 缩,除了太极拳还拥有一定数量的爱好者之外,其他拳种多数都显露出不同 程度的颓势。在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大格局中,专业武术运动队还能被一些 省市所保留,原因无非是它还拥有全运会项目的资格,有几块金牌的价值, 不然景况会更加落寞,更加尴尬。
造成武术如此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举其要者,首先要说与管理体制的 改革长期滞后有关,一句话,现行管理体制早就不能适应武术所面临的新 形势、新问题了。多年来,管理部门只把武术当做一个体育项目来经营,并 不在意武术作为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不在意社会大众对 武术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花拳绣腿的那一套技术体系与理论 早已兴味索然,乃至于产生厌恶,而管理部门却故步依然,无所作为,于是 也就必然地在换汤不换药中左顾右盼、进退维谷。曾经以入奥为奋斗目标的 竞技武术,有过一番虚热,然而终归目标落空,然后一切照旧,迄今看不到 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举措。没有宏阔高远的战略规划,只是一如既往地举办 各种赛事,封赠大小“专家”,继续推销早已严重贬值了的“段位制”。对 之,海内外许多武术人士并不认同,甚至于不屑一顾。
另一个原因是从管理体制中衍生出来的,即长期以来管理部门不重视对 武术的学术研究,不能深入开展武术的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建设, 没有建构起高水平的科研梯队,没有形成凝聚各方研究力量的武学园地,甚 至连一本像样子的学术刊物都没有。当下,原有的几种通俗刊物有的停刊 了,有的勉强维持着,发行量不断减少,内容和质量每况愈下。正因如此, 理论上趋向肤浅混乱,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武术观和对武术学术的权威性评 判,既做不到对大众武术认知的正确引领,也不能为高层管理者提供启迪思 维、扩大视域的营养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武术活动的环境宽松了,市场化 趋向不断升温,这是好事,至少官方垄断的狭隘局面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 但纷乱无序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小说家和影视编导们以“武侠” “剑客” 为主题臆造出来的“真传” “绝招” “秘籍”之类不断喷涌而出,制造了 五光十色的武艺泡沫,严重影响了武术自身的价值系统;紧随其后,“大 师” “掌门人” “神拳”也纷纷抛头露面,招摇过市,武术的生态环境遭受 重度污染,文化层位不断下移。总之,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武术,可以说价 值失落,尊严荡然,几乎沦落成为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的附庸,成了门派林 立、斑驳杂芜的江湖世界,其景象比之民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武术学术研究——我将之概括为“武学”一一的滞后,除了长时间不被 重视外,一个客观原因是研究确有一定难度,而难度之一是资料匮乏,特别 是古典文献资料如凤毛麟角,而且又存在严重的真伪混杂现象。长期以来, 武术资料的搜集鉴别和编纂整理工作做得很少,使得对武术历史问题的探颐
溯源、去伪存真成为学术瓶颈,直接影响到研究工作的纵深发展。迄今除了 少林寺和山西科技出版社做了一定的搜集汇编工作外,武术界很少有人探索 武术古籍在海内外的流布与收藏情况,散落在各地图书馆和民间收藏的稿本 抄本也基本上尘封高阁,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以说武术文献的传存基本上 处于荒漠状态,号为国粹的中华武术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文献系统,没有形成 作为武学基础的武术文献学。以至于培养专业武术人才的高等院校,在本科 和硕博士学位的培养中,从来没有开设过文献学课程。文献根基薄弱,又缺 乏必要的史料学和学术规范的严格训练,使得一些专业研究者同样显得史料 解读能力低下,在史料的探撷应用上辗转稗贩,不求甚解,以致错误连连。 让人不能不喟然长叹的是,一些由当代武术权威人士主持或参与编撰的讲 义、教材和官颁的“必读教材”之类,同样错误成堆,甚而闹出一些匪夷所 思的笑话,令武术蒙羞于天下!
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 性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重心是挖掘散藏民间的珍稀拳谱和各种抄本, 各省体委成立了 “挖整办”,积极鼓励民间拳家捐献出来,授予奖金奖状。 据说当时各地都有重要发现,仅上交到武术管理中心的就有四百多种。应当 时主持武术工作的徐才同志之嘱,我曾以一月之功对中心的藏本逐一过目, 感觉虽不能说都是珍稀文本,但确有一些重要东西,对武术研究颇有价值。 然而挖整一阵风似地过去了,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各省的挖整办早已不复 存在,上交和没有上交而分藏各地的挖整成果都到哪儿去了?成了一桩无人 知道底细的谜。坦诚讲,没有古典文献和历史资料作为立论根据的武术运 动,不仅不能传承中华武学所蕴含的丰富学理、技艺渊源和人文精神,而且 只能在非学术的道路上愈行愈远,直至迷失方向,迷失自我。一方面“竞技 武术”所坚持的花哨技艺导致官办武术不断滑向“武舞”,另一方面是各式 各样的奇谈怪论大行其道,成了某些民间拳家振振有词的理据。早在民国时 期就已遭到学者质疑和订正的“武当道士张三丰”和“内家拳”之类,现在 却更加热闹,甚至比当年还要红火,太极拳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张三丰创造 的“内家拳”。与此相近的例证还有很多,真是不胜其举。虽然武术界严 守学术本位的还是大有人在,也有不少持论严谨的著述问世,可惜这些人和 著作并不被主管部门所重视。在官办武术体制下,出于真心的批评者还可能 遭遇排斥,遭遇冷遇,而钦选的“专家”中不少是缺乏独立精神的权势依附 者,是学识肤浅和人文修养不足的技术工作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经历 了对一切偏激的反传统思潮的深刻反思,经历了全民族的理性回归和文化重 建,这种情况在我国所有的传统文化中都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唯独武 术还继续被“竞技武术”的技术与理论所牢牢捆绑,为神秘主义的迷雾所遮 漫,还继续演义着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义和团式的亢奋中享受着 打败“康泰尔”带来的愉悦,这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
当前,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正在日益突现出来,并汇合成为巨大的社会 动力,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何弘扬武术所承载的民 族精神,加深和扩大对武术文化价值的认识和开发,使这份流传千古的文化 资源转化为促进民族奋进的正能量,如何为提升国家软实力,为民族复兴大 业发挥积极效应,是应该深刻思考并为之积极探索的时候了。
基于对武术现状的沉重思考和对武学重建的学术责任感,在武术界内外 许多热心友人的支持下,我很早就着手搜集武术古籍,特别是存世不多、 流传不广的明清武术刻本和各种抄本,以目前所经见者,经过精心挑选,汇 编成为这部《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之所以冠以“珍本”二字,一是因 为其中确有一些稀见文本,对研究武术发展史,特别是古典武艺向现代武术 的转化历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二是这些抄本多为私人藏品,有一部分则 是海外的公私藏本,研究者确有阅读之难。我和我的编辑班子,在少林寺和 齐鲁书社的大力支持下,决心将这批珍稀典籍公诸社会,真诚希望能为更多 的研究者提供便利,借以为武术文献学的建立铺桥筑路,以期对武术学术水 平的提升稍有推助之效。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这项工作能继续做下 去,更希望能群策群力构建起中华武术的文献体系,进而建构严正细密而富 有学术意义的“武学”体系,使蒙尘已久的中华武术逐渐得以幽光再现。
此外,还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以古稀之年汲汲从事于这项工作, 也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已故武术家唐豪( 1897—1959年)先生的平生遗愿,同 时以我个人的绵薄之诚纪念这位心志高远而苦心孤诣的武学前辈。唐豪是中 华武术和民族体育文献学的奠基人,是武术史学科的开拓者,今年适逢他去世五十五周年,谨以《丛编》聊表个人皈敬承继之愿,亦古人所谓“心香一 瓣,奉之冥冥”者。
二、从武艺到武术
武术是我国古代传存至今的身体文化遗产,是中国本土体育的核心内容 之一。它既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文明特质,又长时间承载着 儒、释、道等多元融会的社会教化功能,特别是对强健体魄、尚武精神和品 德修为的倡导和坚守,可谓绵延千载,厥功甚伟。因此,武术在中国人心 目中一直占有一定的地位,自古以来被世道人心、九流百家所重视。有深 厚武学修养的清初学者颜元(1635—1704年)曾大声疾呼:“文武缺一岂道 乎!”①就是对武术价值最简洁明快的肯定,也是对孔子儒学体系最削切入理 的阐解。
就其源头而言,武术的萌生无疑是非常古老的,后来又经历了漫长的发 展历程,其路漫漫,变数频频,一直到了近代,才终于走上结构和学理的根 本性转化之路,进入了现代武术的发展阶段。这一漫长的转化之路可以概括 为“从武艺到武术”的继承与创新之路。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狩猎活动和各种性质与规模的社会冲突以及祭 祀娱乐等活动中,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提炼升华,终于凝结成为武 术文化体的三个主要元素,即技击功能、健体效益和演练情趣。以三大元素 为基点,逐步建构起了中华武术的内涵及其复杂多变的表现形式,同时也逐 步承载起许多其他社会功能,特别是人文教化功能。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 在不断发生的演进变化中,三大元素有分有合,或显或晦,特别是对不同的 社会群体及形形色色的个体练习者而言,价值取向上往往会各有偏向,呈现 出鲜明的个性差异。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任何传承久远的传统文化概莫如 此,诗文、书画、音乐、戏曲等也都存在这种情况。但作为一个文化整体, 我认为武术的三大元素三位一体,如胶连漆合,从来都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分
[清]李壤纂、王源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721页。
离。正因如此,三大元素的高度协调和浑然一体,便一直是中华武术最重要 的凝聚力和最高的价值追求,也是今天“武学”之所以成立的文化根基。其 中任何一种元素的偏向发展,最终都会游离到武术文化的本体以外,走向非 武术化之路。所以,保持三大元素的协调一致,是近代以来古典武艺向现 代武术转化中所遇到的最关键也最难掌控的问题。可惜的是也正是在这一 点上,道路坎坷,步履艰难,直至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 成功。
古人借用战国时代齐国的兵学术语,曾把军旅的勇力斩杀技术统称之为 “技击”,①此外又有“手战之道” “材武” “兵技巧”和“技击之学”等多 个名称,但后来用得最久也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武艺”。应该说这是一个 非常恰当的名称,故而沿袭久远,一直到今天还时常被人们挂在嘴边。
“艺”有“学问” “技能”等多种寓意,周代礼、乐、射、御、书、数 六门学科也称“六艺”;多才多能也称“艺”,其中应包括肢体技能。古人 又有“艺者道之所寓”的阐解,所以“艺”与“道”近乎同义。②至于“武” 和“艺”两个字缀联成词,似主要源自孔子,出于孔子对“艺”字的多义应 用和诠释。特别是孔子对擅长武艺的弟子冉求“求也艺”的著名奖评。对 此,古人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言(冉)求多才能也”。也有人认为 “冉求之学未必于六艺皆通,圣人特取其所长而称之耳。故曰赐也达、由也 果、求也艺。……六艺之学全材实难”③。我认为冉求(冉有)是孔门高足 弟子中最为通晓兵事而擅长武艺者之一。《左传-哀公十一年》齐鲁艾陵之 战中,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鲁军左师,最终吴鲁联军战胜强大的齐军。原因
《荀子集解》卷十《议兵篇第十五》:“齐人隆技击。”《集解》:“技,材力 也。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号为技击。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 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见[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等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271页。
[清]乾隆敕撰:《钦定周官义疏》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元]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卷一“问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何独称求 也艺”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第353页。
之一是“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①“用矛”二字有着明显的武艺 含蕴,这正是对“求也艺”的恰当注解。此外孔子还有“依于德游于艺”等 语,有人认为这里的“艺”即指武艺而言,如明儒王志长(字平仲,夏山 人)说:
士游于艺,未有不习射御者。夫子亦曰“我战则克”。自文武 殊途,服儒衣冠以武事为耻,而介胄之夫不知义。②
这些都说明“武艺” 一词的源头出自孔子,至少与孔子有重要关联。汉魏以 降,“武艺”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一直被延续到清末才退出历史舞台, 渐渐被“武术”所取代,而这一取代的过程中,还出现了 “拳”字的过渡 作用。
“武术” 一词,虽然古代有用过的例证,但只是孤证,广泛使用似乎相 当晚了。迄今我们在晚清文献中并未找到它的确切出处,暂时只能从民国 初年北洋军人马良所倡导的“新武术” 一词上反证“武术” 一词在民国前就 已存在。但“武术”取代“武艺”并被社会普遍使用,应该是在民国初年。 在我看来,“武术”取代“武艺”,正是古典武艺转化为现代武术的重要 标志。
“武艺”走向“武术”是一个逐步完成的漫长过程。实际这一转披早在 明末清初就已见端倪,至清代中后期渐渐演化成为潮流,开始出现义理与技 艺互为表里、融会发展的拳派,当时多称为“门”。“门”的称谓与明代拳 种或拳派明显不同,有些“门”的名称具有了儒、释、道的哲理特点,如形 意、太极、八卦、通备等;有些则依托民间神秘信仰如白莲教、天地会以及 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少林寺等。传统武艺正是在以“拳”为中心的门派潮 流中,一步步走向现代武术O
浏览1,30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