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即各种兵器相互配合,以骑马之 弩兵游击;三是“材官骤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①,是说汉朝 有万弩齐发的优势。
汉代军中有强弩、积弩将军之名,可见弩的使用普遍,地位尊崇。连射艺高 超的李广在紧要关头也要靠弩解围。《汉书・李广传》载,在一次对匈奴的战争 中:“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 数人,胡虏益解。”②据颜师古等人注,大黄是一种角弩。当时情况应该是李广命 兵士为弩上矢,再递于李广并由其完成射击。这种使用弩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弩 机张弦与发射相互独立的优势。
两晋与南北朝时期,大弩空前盛行,军中与仪仗及武官考试皆用弩。《晋 书-舆服志》记载“中朝大驾卤簿”内有:“神弩二十张夹道……其五张神弩置一 将,左右各二将。”③当时,马隆请募勇士,限腰引弩三十六钩,弓四钧,立标简试, 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④义熙六年十二月,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 至莫不摧折,成为决胜的力量。
隋唐时期,弩机种类更加繁多。据《唐六典-武库令》记载:唐代弓之制有四 种:长弓、角弓、梢弓、格弓,分别为步兵、骑兵、近射、仪仗使用;而弩的种类超过 了弓,有七种:擘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伏远弩。⑥ 唐代骑兵也用弩,并且制定了相关考核赏赐方法;“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 百步,臂张弩二百三十步,皆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一 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⑦。另外,唐还有守城大弩静塞弩、连弩、摧山 弩等。
宋代以后,火器出现,但弩的使用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呈现出繁荣的状况。
《玉海》卷一五。说宋代射远器大部分为弩,相比以前,宋弩在追求弩的力量与射 程上用功极深,数人同发的床子弩等大量出现,并且弩往往被冠以弓的名称,如 神臂弓、克敌弓、强远弓等。据记载,熙宁年间于玉津园验射神臂弓,“二百四十 余步,穿榆木没半杆”①。相比于“百步穿杨”的弓箭,这些弩的威力显然更大。
入明之后,随着火器的日益繁多,弩逐 渐衰落,至明末已经基本为火炮所取代。明 人丘漕曾作《器械之利》,论曰:“今世则惟用 弓矢,而所谓弩者,队伍之间不复用矣,意者 有神机火枪之用以代之,故不复置欤! ”②可 见,明代弓矢仍然存在,而弩则基本被火器 取代。不过,综观中原地区由汉族统治的王 朝,弓矢虽然未被废止,但随着弩机与火器的兴盛而日益衰落,在射远器上总体 呈现出冷热兵器交替的趋势。
从秦代的弩兵方阵至汉代的“材官”,再到宋明时期各种各样的大型弩机,以 及相继出现的早期火炮,都可以证明,虽然在汉文化中,尤其是在传统儒学中,射 礼曾长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军队中,弓箭则不断地被边缘化。与之不同的是, 弓箭一直都是游牧与渔猎民族最基本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武器,除了制造技术 与材料使用上的提高,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女真一直以骑射闻名天下,但直 到1599年,建州女真炒铁成功,用铁制箭镰取代了原来的鹿角等材料的箭镰,才 真正将弓矢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
杂、大型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对操控者本身素质的忽视;而满族则是 对单一兵器的依赖,其结果必然导致对操控技术与操控者本身素质的较高要求。 这两种不同发展轨迹的形成有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基于农业生产而形成的 汉文化是一种平和、细致、防御型文化,而基于渔猎生活的满文化是一种质朴、勇 敢、进攻型的文化。在军事对抗中所表现出的满汉兵器、战术、战略的区别,其本 质还是一种文化的冲突。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在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 (The Silent Language)中总结出适用于各种文化的十种基本信息系统,包括互 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①也就是说,这些信息 系统关联着一个文化的整体,是区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基本单位,也是一 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能够相互交流的基本切入点。
在满洲文化中,射箭几乎与十种基本信息都有紧密的联系。弓箭在满洲人 的社会中,既是武器也是劳动工具,射箭活动是教育、休闲、交流、团结的主要方 式,也是满洲男女两性区别的标志之一。例如,满洲旧俗,对新生婴儿,重视区分 男女。如生男孩,则在门楣上悬挂一张小弓和三支小箭,预祝新生儿将来成为一 个好猎手;如生女孩,则悬挂一条红布,象征吉祥。乾隆帝曾说:“生为男子,一切 皆应务实,习技艺、服劳苦则有益于身,且筋骨强壮,疾病自少……愚人好逸,不 学技艺,以致畋猎军旅、盔甲弓矢,罔知修缮,惟于筵前修饰衣服是务。身系男 子,与无识之妇女何异! ”②
因此,弓箭其实是满文化中最为关键的节点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由 乾隆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列骑射为国俗第一,其次才是政教文字、祭祀典礼、 官制语言等。而在汉文化中,文教才是核心的内容。这就造成了满汉文化在产 生冲突时,在文化的核心形式上缺少共鸣。
德国汉学家魏复古曾经提出征服王朝的理论,将辽、夏、金、清均视为征服王 朝。这些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统治时要面对巨大的民族差异。可以想见,满洲
以一个少数民族,要统治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华泱泱大国,除了面对种种社 会问题之外,还要在根本上防止失去民族文化本位,并保证赖以统治的武力基 础。在这种情况下,满洲引以为傲的射箭传统就成为平衡满汉文化的砥码。
清朝的缔造者之一皇太极,对于汉文化甚不以为然。有史学家提出,在是否 要入主中原的问题上,皇太极曾一度犹豫不决,多次向明朝表示议和的意图。其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广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 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 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曾号召众王、大臣读《金世宗本纪》,目的是让大家 吸取金亡教训,勤习骑射,勿效汉习。
……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矣。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 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 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 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 灭亡,乃知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②
应该说,过度的汉化是每个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国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金朝的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随着女真人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一统天下的大 业也摆在了皇太极的面前。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曾经多次劝皇太极改满洲 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制度,当时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小的争论。皇太极对此并不认 同,并严厉告诫群臣。在皇太极看来,“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 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等译,14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141册,5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141册,5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相比于皇太极,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对汉文化的认识更 加复杂,他们既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学习,对汉族的人生志趣也十分着迷,但依 然恪守祖训,首重骑射,乾隆甚至将皇太极的训诫刻碑四通,分别立于紫禁箭亭、 御园引见楼、侍卫教场、八旗教场,“使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 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
究其原因,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明清战争的胜利,是骑射以及英勇淳朴的满 洲习俗的胜利,而骑射与满洲的渔猎习俗之间存在着根本联系。因此,武器使用 的区别是由更深层的文化与习俗原因形成的,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到文化与习俗 的层面。同样,汉文化中表现出的奢靡、懦弱、虚浮、空洞的缺点,和汉民族所使 用的“便利”兵器不无关系。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闻知索伦人在围猎时逐渐 使用鸟枪,弓箭渐被疏置,大为不满,认为他们“惟图利便”,命令时任黑龙江将军 的傅尔丹将鸟枪一一“买回”。
(二)清统治者如何用骑射保证满洲文化的根本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叙例》中讲到文化、政治、生计三者的关系时称:“文化 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 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
射箭正是关系到政治、文化、生计的满族“密码”。为了维护民族根本,必须 以强制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大力推行骑射为代表的射箭活动,多管齐下,加强 满洲人在射箭上的教育与训练,锤炼技艺,增强体质,磨砺精神。这些手段主 要有:
1 .加强八旗军弓马训练。据清代官书的记载,在清代的军事训练中,八旗满 洲、蒙古以训练射箭为主,每月一般要练习马、步箭六次,春秋二季还要专门摄甲 骑射两次或四次。而八旗汉军及绿营兵则以枪炮、大刀、藤牌为主,射箭训练仅 为辅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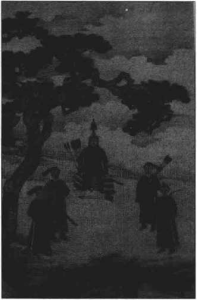
皇帝亲射,激励士卒。雍正曾拿自己与康熙比较,说:“皇考神武天授,挽 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射技,不及皇考矣。”①满洲 善射,努尔哈赤射艺高超,历代清朝皇帝皆须娴习弓马,其中又以康熙、乾隆最精 于此。二帝常于大阅、训练、围猎之时亲射,上下钦服,起到了良好的激励效果。
教育约束。为了使满洲人保持勇武淳朴的传统,远离汉人陋习,清代统治 者选择用骑射、清语对满洲子弟进行教育约束。而在两者之中,又以骑射更为紧 要。乾隆曾经说过:“满洲等读书学习翻译固系当务之事,而马步箭究系满洲根 本,断不可不至精纯,不能射马步箭,即使翻译尚好亦属无用。”
从后金的建立开始算起,清代延续了近三百年,在这段时期里,满汉文化通 过各种形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流。相比于历史上类似情况的政权,如辽、夏、 金、元等,清代满族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最高的,正因为如此,清代统治者才花 费更多心思防止满洲过度汉化。但即便如此,历史的发展也不会以统治者的美 好愿望为方向。失去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满洲人在入关之后的腐化非常 严重,既没有学到汉文化的优点,又丧失了满文化的本真,八旗子弟更是养尊处 优、不学无术,即使有打猎之举,也不过是走狗飞鹰,嬉戏游玩,与统治者追求的 质朴尚武相去甚远。
三、从射箭看满汉文化交流成果与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在清代,满汉文化既相互冲突,又不可避免地高度融合,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射箭作为这种冲突与交流的 核心内容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留给我们许多经验、教训和遗产,值得我们重新 审视。
(一)对清朝“弓马立国”的再审视
清朝后期的腐朽、愚昧是有目共睹的,弓箭甚至被视为这种落魄的代表。普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一,《文津阁四库全书》,142册,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李洵、赵德贵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三,1639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
遍的观点认为,清代统治者由于偏爱弓矢之利,从而忽视了火器的发展,因而将 清代的射箭文化视为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文化。这样的看法虽不无道理,但是失 之片面。实际上,晚清面对西洋坚船利炮时的不堪一击,弓箭当然难辞其咎,但 绝不仅仅是清统治者对弓矢的偏爱单方面造成。清代统治者对火器的认识甚至 要超过明代的统治者。皇太极组建八旗汉军这样一个炮兵部队,已经证明后金 开始重视火器的使用。从大凌河之战开始,清兵也越来越倚重于火炮。明亡后,
徐光启关于引进红夷大炮的《徐氏庖 言》一书留存于钦天监内,顺治帝对 此“读不释书,叹曰:'使明朝能尽用 此言,则朕何以至此也!①而惯于围 猎的康熙与乾隆都能熟练地使用鸟 枪,并对其功能有着清晰的认识。但 是,正是因为鸟枪便利,清代的皇帝 因而视之为汉文化的产物,对其加以 严格限制,以防八旗官兵因使用鸟枪而沉溺于安逸。清代的统治者面对火器时, 一方面视其为先进的利器,另外一方面又视其为汉人的兵器,担心过多地使用会 造成骑射传统的丧失,使满洲的尚武精神遭到破坏。这种心理的发展,最终演变 为阻碍热兵器在清朝继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恃权而骄, 失去了军事生产一体化生活背景的满八旗,勇气与骑射技艺也消磨殆尽。据嘉 庆帝回忆,早在乾隆时期,长期养尊处优的八旗军已经“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堕 地”②,可谓文不成,武不就,统治者的如意算盘全面落空。
一物两面,清代倚重射箭的负面影响在学界几乎已成为共识,但是其正面的 经验及影响则没有得到相应的认识。综合来说,其正面影响可以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对以骑射为代表的尚武精神的培养以及对汉文化的遵习,在一定时期
内维护了整个中国的和平统一与强盛。清代长期维持辽阔的疆域,基本保持了 内地与边疆的安宁。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谕大学士曰:“有人谓朕塞外 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敌有 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①在大兴围猎增强武备的同时,康熙也吸取汉文化 中的治国思想,规定武举加考《论语》、《孟子》,以宣扬“仁者无敌”,推行王道。② 所以说,是满汉文化的共同作用才造就了强盛一时的大清帝国。清末,西方强敌 当前,汉族知识分子魏源以《圣武记》从军事角度解读清代盛衰,激扬民族斗志, 也是这种融合的结果和证明。
其次,满汉文化的共同熏陶,使 清代的皇帝大多尚武勤政,从而使政 权免受宦官外戚之患。其中尤以康、 乾为代表,他们不仅孜孜向学,深得 汉文化要旨,而且娴熟弓马,精力充 沛,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 康熙与乾隆每年七、八月份都要移驾 木兰围场或承德避暑山庄,围猎行幄 之中,也未荒废政事,而且往往精神 得以振奋,对政事大有帮助。康熙四 十八年(1709),康熙帝于木兰围场亲 谕诸内大臣:“朕自热河启行之时,因身体虚弱,思择水土佳处,游行调养而来,不 意即能乘马行围,略不疲困,虽肌体未复原,而寝食固已如旧矣。'淄康熙在驾崩前 三周,还至南苑行围,说明巡视塞外、骑射行围既是清代的军国大事,也是清代皇 帝保持身心康健的重要手段。
再次,清代对已经文武分途的汉文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康乾时代 都曾经尝试鼓励文人参加武试,武人参加文试。雍正认为“古者射御居六艺之
圣人之所重”①。因此更加严格执行满洲士子应试必先试其骑射合式方准 入闱的制度。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当时的学风。清初注重实行、崇 尚艺能的颜李学派在思想上与清代统治者所提倡的学风多有相似,并形成了一 个践行这种思想的学术圈子。而这种思想的形成,和明清易代的社会现实有关, 也和满洲尚武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有关。
最后,中国射箭文化体系在清代最终形成。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冷热兵 器更替的关键时期。满洲对弓箭的熟练运用,使冷兵器在与热兵器的对决过程 中保持着某些方面的优势,比如机动性与射击效率等。再加上骑射在满洲文化 中的固有地位,弓箭等冷兵器在它的末世仍然得到相当的重视,从而留下了丰富 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弓矢与相关物品实物,以及大量的图画、历史 记载、文学作品和专门的射书。这些遗产使我们能够对弓矢形制、技术、相关活 动进行直观、全面、详细的了解。而这些实物之所以能够得到相对完善的保存, 相关文献之所以能够大量编写刊印,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汉文化。换言之,中 华民族的射箭文化是在清代完成了合流。
(二)中国射箭传统对当今的启示
2012年,在十八大闭幕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协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前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中,他又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共同的愿望,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又是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和应有之义。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绚烂的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是其中最富中国特色的遗产之一。然而,随着时代
《世宗宪皇帝圣训》,卷——,《文津阁四库全书》,142册,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马明达:《颜李学派与武术》,《说剑丛稿》(增订本),10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的发展,加上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众多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形式在近代都受到不 同程度的冲击与毁坏。一些主要的中国民族体育形式,如射箭、武术等,都已发 生剧烈异化,而大量中小型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或名存实亡,或彻底消失,如弹弓、 冰戏等。复兴潮流涌动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显得更加格格不入。
面对这种困境,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回到传统本身,追寻它们的发展轨迹,探 究它们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才能以客观的态度去粗取精,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清代的射箭为例,回顾它在历史上的发展、兴盛与 衰落,不难发现,它是满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中枢之一,而我们之所以会把两条迥 异的射史轨迹混为一谈,也正是因为它们在清朝完成了合流。可以肯定的是,这 种现象绝不仅仅发生在射箭一个领域,清朝所处的传统社会末期的历史坐标,使 其可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代。可是,如果缺少了中华民族本身包容 性的文化特质,清代的文化成就也不会变成现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 视,也正是在清王朝所处的时期,在工业大潮的席卷下,中国开始了落后、挨打的 厄运。但是,面对千年未有的局面,一味“驱除帖虏”,完全归咎于满洲的统治,则 无疑是片面与武断的。如果因此更进一步,将与满洲相关的文化都一概否定,便 可以说是因噎废食了。事实上,尽管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伴随着激烈的冲突,甚至 战争,但每一次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合力,都指向了统一与融合的历史主流,多 民族造就的悠久而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我们今天走向世界的最大软实 力之一。
真正有意义的传统从不也不应该止步于历史的天空。然而,时过境迁,已经 式微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在原地起死回生。仍以射箭为例,作为传统的遗产,在当 下社会,其意义早已脱离军事的范畴,而更多地体现在教育与运动休闲领域。
放眼当下,关于国内青少年体质的负面事件不断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表 示担忧。但是同时,各种电子玩具、电视、电脑、手机等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日 渐泛滥。近期,武汉一个两岁半男孩玩iPad 一年致近视500度的新闻,给教育者 和家长们敲响了警钟:如何才能让孩子拥有更加健康的身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当年康、乾等皇帝的担忧有一 定的相似性。至清末,梁启超、蔡锣等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忽视 身体教育的事实提出了振聋发瞪的批判,并提倡向日本学习体育。梁启超在《论 尚武》中批判中国文化:
后世贱儒,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悯涂炭、矫枉过正之言,以为口实,不法其刚 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阴取老氏雌柔无动之旨,夺孔学之正统而篡之,以 莠乱苗,习非成是。……及养成此柔脆无骨、颓惫无气、刀刺不伤、火燕不痛之民 族,是岂昔贤所及料也!
蔡镑也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
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间,此中十年之顷,为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俗师乡 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窟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 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中国 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②
时移世易,今日摧残青少年的已经不全是阴柔的陋习,但是,历史仍然能为 我们提供启示。那就是,不论过去现在,“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都应该是教 育的应有之义。
同时,我们还不无遗憾地发现,在身体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上,我们缺少传统 的内容,在运动场上我们一路跟随世界潮流,缺乏自身的特色。我们一边角逐于 现代射箭的运动场上,一边却将中国传统射箭视为封建愚昧的标志,弃如敝屣。 反观日本弓道及韩国弓道,不仅在本国备受尊崇,在世界上也日渐风靡,日本弓 道甚至已经在天津体育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开设弓道馆,走进了中国 大学的课堂,并受到了师生的欢迎。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中国传统弓箭不 仅仅是一种过时的兵器,更是在中国历史中关系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一个重
梁启超:《论尚武》,《梁启超全集》,70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蔡铐:《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要文化载体,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宝贵遗产和重要见证。落后守旧并不是传统 弓箭本身固有的性质,我们在走向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需要对落后的思 想加以警戒,更需要在创新中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加以继承发扬。
一、“索伦”箭与“索伦”弓
清允禄等编《皇朝礼器图式》①收有两种“索伦”箭:“索伦被箭”和“索伦哨 箭”。所谓“被箭”,是箭的一种统称,除哨箭、饱头箭、鱼叉箭、兔叉箭等几种外, 箭镀为铁,呈扁平、四边形者均可归入被箭名下,如大被箭、行围锻箭、遵化长被 箭、索伦被箭等,射鹿箭亦可归入被箭门类。被箭箭头窄而平,与箭杆紧密结合, 而哨箭箭头则宽而圆,与箭体连接处有突颈,至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仍有收藏。 《清宫武备》②“御用白档索伦长被箭”条记广铁制箭镰,杨木箭杆,杆首饰金桃皮, 括裸朱漆,外裹黑雕翎。用作军事用途,亦可射熊、野猪等。每组十一支,十支为 高宗皇帝御用之物,另备一支用于检查。”今存“索伦”各箭本身的工艺并无特殊 之处,包括其箭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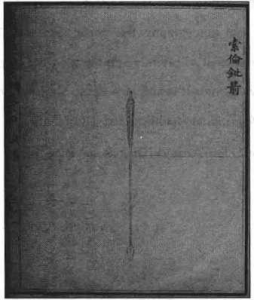
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藏 有世上现存唯一的“索伦弓”,是 沃特-斯托茨纳于20世纪20年 代末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收集到 的:其设计和尺寸与鄂伦春弓相 似,为经典式呈形的整木弓, 相较于故宫博物院和《大清会典 图》中的“索伦”箭而言,这种类型 的弓一般用较短的拉弓动作,与 开满弓的满族箭不太一样,为另 一种类型的“索伦弓”。二者或分 属不兼容的两种弓箭类型,并有独立的演进系统。拙文《中国北方猎手的射箭传 统》曾就此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清王朝履政之初,最重“国语骑射”,视为立国之本,此风后世渐不能保②,但 当乾隆年间,高宗弘历三番五次告诫本族人要保持“国语骑射”,亦以身作则,躬 行其事,也是实情。③“索伦”箭支能够作为“御用之物”且荣膺“礼器”之名,充当 乾隆时最重大制度之一的“行围”仪式中的道具,当与“索伦”名号在清前期的政 治、军事地位相关。
二、索伦部、索伦兵气索伦营
“索伦”称谓内涵及其指代之确认,为开展研究之必需,研究者争议不断。实 际上,“索伦”之名在清代即有多层次的含义,早期是作为一种“他称”而存在④,作 为“自称”就比较晚了⑤。详考清代文献中“索伦”概念之内涵,可以略分作以下三 类,指代各有偏重,而时现纷出,则不免令人目迷五色:曰索伦部,乃清初活动于 黑龙江部族之概称,其民族成分大约包括现代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 等,其重在区域人文地理,如版图、纳贡,甚至旗籍等皆是;曰索伦兵,则奖其骁勇 善战,身秉北方少数民族因游猎生产生活方式而养成之善战,'血统”,其指代则为 原指索伦部族并入旗籍之后去农从戎之人丁,其重在勇力⑥;曰索伦营,则纯为 军事建制单位,以“伊犁四营”名世者,其民族构成则更为复杂,并兼锡伯、蒙古 等,实为军政现实逼迫而形成。循此理路剖别区分,则可免许多无谓纷争。
“索伦”相关概念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从“索伦''本身的语义到活动范围、生 产生活方式、族群分类归属等。徐凯在《清代东北地区民族问题探岐偶感》中说道:“索伦一词 在清代即具有两层鲜明的含义",一为部族总称,一为地域称谓(韩狄:《清代八旗索伦部研 究——以东北地区为中心》,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清人有游戏曰“满洲棋",属于中国象棋的一种衍生玩法:“其法,敌手亦置十六子。 行满棋者,置将一、士二、象二、兵五外,余仅一子,能兼车马炮三用。故一交手,即纵横敌境, 守者稍不慎,满盘皆无补救。此虽游戏,然可想见入关后索伦兵之气概也
此处特指清政府为平定叛乱、加固边防而在新疆伊犁设立的营制,“索伦”与锡伯营、 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并称“伊犁四营”,主要分布在塔城地区。
朝克《关于鄂温克民族的族称》一文中对过往各家“索伦”各有评析,认为“索伦”是清 朝政府对鄂温克人的一种称谓,“索伦"一词系由满语的基本动词''索劳”派生而来,动词索劳 主要指“顶”、“逆”等意思,在实际指代中表示“顶梁柱"、“柱子”等多义,颇精当。考《清稗类 钞》收与“索伦"相关条目近二十条,涵盖朝贡、地理、爵秩、屯漕、战事、方言、方伎、豪侈、会党、 农商、文学、艺术、种族、宗教等十四类,虽其意指不尽相同,但其行文中“他者”的叙述立场确 是十分统一的。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三:“世于黑龙江人不问部族,概称索伦,黑龙江人居之不疑,亦 雅喜以索伦自号。说者谓索伦骁勇闻天下,假其名足以自壮。"
典型如出身''索伦马甲''的名将海兰察。
“索伦”的政治地位来源于其地理指代,学界大致将“由黑龙江上源从石勒喀 河向东南伸展,直到精奇里江、牛满江,即外兴安岭以南与黑龙江中上游之间的 广大地域”作为“索伦部”的活动范围①,而在族群指代方面,则指包括了现代鄂温 克、达斡尔、鄂伦春诸族的民族复合体②,如此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便使得“索 伦”的存在,无论是在清王朝的建立③、东北边疆的巩固④,政权的稳定⑤,还是在 八旗制度和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皆为重要的政治构成部分。⑥
在军事上,索伦部族被并入八旗体系之后,因其生产生活方式而具备成为冷 兵器时代强大战力的优越条件,对于清政权而言,无论作为对手、部属,还是再编 成的战斗力单位,“索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军事实力的代名词。而八旗制 度军政合一,满族人本身即是以围猎为主的游牧民族,建国后更行倡导“国语骑 射”,清初诸帝如皇太极、康熙、乾隆个个精于骑射,十分重视武备,曾在战斗中令 八旗军兵吃过苦头的“索伦,,⑦,一经归化,能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及倚重,并不 奇怪。
浏览1,828次